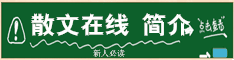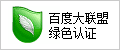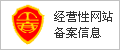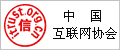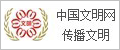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母亲是凌晨住进医院的,父亲雇了一辆面的,一面往县城疾驶,一面打电话给我,说母亲又吐血了,这次的量还特别多,万分凶险。我在睡梦中被手机惊醒,听到这个凶信,急忙穿上外套,匆匆地骑上电动车来到县医院。 母亲在急诊室里,虚弱地倚着墙瘫坐着,父亲正寒颤颤地在缴费窗口排队,我走了过去,父亲把手里的钱递给我,让我挂号,我一边排队,一边询问母亲发病的原因。原来是昨天给祖坟树碑,几个帮忙的本家在我家吃了点便饭,母亲做饭操劳是一方面,也吃了很多大油腻的菜,消化不了,夜里就一直辗转反侧的难受,到凌晨的时候,突然的翻心,吐出了小半盆的血,整个人都像风筝发飘了,父亲给村里医生打电话,张医生也不敢擅自主张,吩咐父亲抓紧送县医院抢救。 挂了号,我和父亲急忙返回急诊室,拿着医生开的住院单,搀扶母亲到后面的住院病房楼。可是,事情又出了意外,病房楼里面早已满员了,连走廊道里都排了好几张床位,医生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不住地强调没有空床,让我们到南院分院去。南院?还有五六里的路程呢?我耐住性子和住院医生商量,能否克服一下,加个床位,即使在走廊里也行呀,病人情况特殊,大出血,经不住来回折腾的。听说病情凶险,医生的眉头皱的紧紧的,更是油盐不进,并且开始电话联系南院了,南院的那个医生倒是很爽快的,答应接收,并且说,这种病就应该到他们治疗的。 于是就抓紧联系救护车,等了十几分钟光景,在寒风刺骨中,终于联系上接送的车子,我和父亲又扶着颤巍巍的母亲下楼,走过好几道急救通道,来到尚在发动的救护车前。我把行李放到门旁等候,父亲把我拉到一旁,从枕头套里拿出一个小手巾包来,一层层地打开,“这是我带来的三千块钱,你收着,到时好付账,人多杂乱,放你那儿保险些。”我心里酸酸的,伸手接过了钱,一次次的犯病,老家仅有的那点积蓄能坚持多久?母亲的身体究竟还能经得起几次折腾?七十岁的父亲今后的生活如何着落?唉,这些烦心的事情,没法深想,头都疼的,抓紧顾住眼前吧。 零下的温度,车子好不容易发动了,在呛人的劣质汽油味中,我和父亲挟着行李,一个扶着,一个在后面半抱着母亲,送她躺到了救护车上,然后就是一路疾驰,绕过刚刚有点车流人流的繁华车道,驶到东面的主干道,向南院奔去。 南院,基本都是住院部,我们在路北的那座楼门口下车,扶着母亲慢慢地走到医生护士办公室附近,那个刚刚接电话的中年大夫还在值班,他寸头,红红的脸膛,很豪爽,很不耐烦的愤青模样,我们介绍了情况,他说他给安排一下,可是,护士长直截了当的回答却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空床!这可如何是好?大老远的已经跑过来了,总不至于再回去吧,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医生很不耐烦,让护士长想办法解决问题,然后甩手出去了。 我就和护士长交涉,解释说,是你们这儿的医生要求我们过来的。护士长指着刚才出去的医生,“就是他呀,你们怎么信他呢,他是个神经病!你们这样的危重病人呢,应该到市级医院去看的,那儿条件更好,医疗设施先进,医生技术也棒的。”我真有点忍无可忍了,很想淬这个护士长一口,但是,彼时彼地,谁又敢呢?我忍气吞声地陪着笑脸,“我妈这是常见的消化道疾病,不是什么疑难杂症,用不了到那么好医院的。你们这儿的设施已经足够好的了,医生也都是经验丰富的,我是信得过你们的。再说了,我妈这情况,你也看到了,出了这么多的血,身体极度虚弱,还不知能不能经得住那一路颠簸呢,说不定还没到市医院,人就不行了,您就发发慈悲,帮忙弄个床位吧,我在县医院那面看到走廊里都放了好多病床呢,你们这儿完全也可以加的。”护士长一脸的鄙夷不屑,“我们这儿每个病房几张床,都是正好的,没有多余的病床,你妈病情这么重,随便找个床受不住的,出了啥意外的,我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还得讪讪地笑着,“不需要你们负责的,我妈的情况我们自己也清楚,有啥好歹,不怪你们丁点的。 护士长被我纠缠不过,极不情愿地来到走廊东侧的一个病房,那里空着一个床位,但是病人是早出晚归的,所以不能占用,旁边有一个是家属临时躺着休息的窄小的沙发垫床,她指了指,噘着嘴说,不嫌弃,就睡那儿吧。看着母亲一点点的衰弱下去,再这样的站着十分吃力,我就和父亲点头同意了,把带来的被褥匆匆铺好,然后小心地搀扶母亲躺下,给她盖上被子,闭目休息。一番周折下来,母亲的脸色已如土灰一般难看,眼皮很疲倦地合着。我跟父亲交代了几句,然后说车子还停在县医院,抓紧回去骑过来,再说,二老带的拿点钱不一定够用的,还得回家再拿些钱。于是,就急火火的出门打车返回县医院。 8点多一点,我又匆匆地骑着电动车赶回南院。静悄悄的病房理,母亲依然蜷缩在东北角的那个临时添加的简易病床上,窄窄的,翻个身都会滑下来。她的身上胡乱地盖着厚厚的棉被和棉衣,床头的高架子上,拴着长长的透明的吊针塑带,透明的液体正缓缓地输入母亲的体内,维持着她微弱的呼吸和心跳。父亲神色凝重地坐在床头,我俯下身子询问病情,父亲说还是那样,一直没有再出血,解了一点点的小便。 我走到床前,帮母亲掖了掖被子,真不忍看到她已瘦成细长条的满是黑褐色皱纹的脸。我问她感觉怎样,母亲没回答,只有略急促的呼吸,还有微闭的双目。我在一侧坐下,想缓口气,这时看到侧卧着的母亲忽然艰难地欠起身,她的两只干柴一样细瘦的胳膊都插这吊针的针尖呢,我急忙和父亲过去架住她的膀子,阻止她的挣扎,小声急切地问她是否躺得久了,有些麻木难受,母亲的眼睛突然翻出眼白来,骨碌了几下,又没了任何反应,不作回答,兀自依着墙,半坐在那里,污浊地呼吸着。 几分钟后,我和父亲把母亲身下的被子稍微理平整些,安抚着母亲躺下,她不到60斤重的身子,瘦骨嶙峋的,真怕不小心就把哪儿折断了,况且昨天的大量胃出血,血管还没有愈合好,稍稍用力再崩裂了,那就极其凶险了。 母亲在微弱的挣扎中被我和父亲按下去,很不舒服地蜷缩被窝里,最南侧的病人已办完了出院手续,病人坐在一边休息,父亲过去跟他们商量能否先把床位让给我母亲,病人大姨看到我母亲的万般痛苦之状,痛快地答应了,她的老伴还有些迟疑,不高兴地嘟囔着,最后也勉强同意了,于是我和父亲就抓紧收拾东西,往刚刚腾出的床位上搬移。 匆匆地铺好被褥后,父亲用力钳着母亲的两胁,我托着他的双腿,举着吊针架子,吃力地紧走几步,把母亲转到了那个宽敞舒服的病床上,给她盖好了被子,把吊针瓶都整理妥妥帖帖的,爷儿俩总算松了口气,说些闲话,我叮嘱父亲在医院里要想得开,一日三餐要吃好,有精力照顾母亲。正聊着,母亲又躺不住了,支着胳膊又往上欠身子,我们赶忙过去制止,好不容易让她安静地平躺下,可不幸的是,这一次的闹腾把母亲手腕上的针头带了出来,按铃喊来护士,看到母亲水肿的皮肤,静脉若隐若现的,护士皱着眉头,回去喊护士长开重新扎针。 护士长姗姗来迟,强忍着满脸的不耐烦,看到手腕上扎针实在太困难了,她低下头在母亲的脚腕上找静脉,扎上橡皮筋时,母亲疼的哎哟哎哟的叫唤,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受不了一点疼,护士跟她说话,让她忍着,可是母亲好像没听到,一点反应也没有,依然故我地叫唤着,护士长的额头沁出了汗滴,命令我抓牢母亲的脚踝,别再让她乱动,然后她继续努力地往静脉里刺针。 母亲的身体在哆嗦,剧烈地抽搐,两条腿踢腾着,护士长的针刺进皮肤时,母亲又疼得欠起了头,含糊地哭喊着,焦躁地叫着,“哎哟,妈妈哎,哎哟妈妈诶”,我用尽力气,两只手死死地逮住母亲的双脚,让她别乱动,忍一忍,可母亲什么也不管了,疼得呻吟着,两腿不住地竭力往回抽动,躲避着扎针。 护士长耐着性子,不断尝试往静脉里插针,终于把针扎进了血管,还好,正常回血,贴好固定胶布,可母亲依然在喊疼,我问护士长是否筋太细了,针尖在里面别着劲,能否重新扎。护士长摇摇头,没办法,这已经是医院里最细的针头了,你妈的血管老化了,这根筋还不知是怎么找到的,只能如此了。 看到母亲的痛苦万状,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又担心她的蹿动带出针头,只好紧紧按住她的双腿,边安慰她,“过会适应了,就不疼了”,母亲对我的安慰充耳不闻,依然像个任性的孩子喊叫着,挣扎着,眉头紧皱着,晦暗的脸疼得扭曲着。 渐渐的,母亲的叫喊弱了下去,稍稍安静些,头略向上翘了翘,喉头蠕动着,父亲这方面还是很有预感的,连忙把把便盆递上去,母亲张开嘴,冲着盆大口吐着,呕出来的是带着腐臭味道的粘液,以及昨天出血凝成的血块,暗红色的片状的血块。呕吐物将近一小碗,忽然血块里掉出了一个拇指长短的牛筋样的东西,我惊慌地问父亲,父亲说这是妈妈的假牙,我才松了口气,捏出来到卫生间冲洗干净,放到一个空碗里。 折腾了半个小时,母亲疲累了,闭着眼,沉沉睡去,不到十分钟,她又惊厥过来,焦躁地欠起身子,我们以为她的身子又睡麻木了,想活络活络,于是扶她起来换个姿势。母亲大口大口地出着气,恹恹的,我心里叹息着,不知如何是好,母亲缓了缓,又向前倾了倾下巴,我连忙从床下掏出便盆,母亲在一阵干呕之后,又开始大口大口往外喷吐出咖啡色的秽物,夹杂着紫菜色的絮状物,吐了大半碗,母亲微闭着眼,没了动静.我和父亲把她放平,我把呕吐物放到卫生间,没扔掉,我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想等医生过来看看那些呕吐物,做个诊断. 我非常疑惑母亲呕吐物里絮状紫菜色的东西,胃壁那么韧实,不可能被腐蚀剥落的,那究竟又是什么呢?询问父亲,父亲说前天给祖坟树碑,庄里两个堂兄弟荣万和荣文在我家吃的饭,母亲做的是干饭炒鸡蛋,放了很多油,母亲顺便也跟着吃了不少,应该是那天吃的菜叶子还没消化掉吧,现在才吐出来。我心里明白了几分。接着又谈起了近阶段母亲的饮食,父亲说她年前吃了不少的猪肉饺子,管不住自己的嘴,年后还一直嚷着要吃顿牛肉饺子呢。听着这些,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母亲胃病这么多年来,消化能力是弱到了极限,可胃口还是那么好,忌不住嘴,难怪消化不良导致一次次的胃出血,我每次在她住院期间,都再三叮嘱,要少吃多餐,吃易消化的糊状物,可是,慢慢的,母亲就把我的话语淡忘了,真是祸从口入呀,老人也就那点胃口上的嗜好,我又怎么能过分苛求呢,实在是无奈呀。 又一个中年护士查房过来看看注射情况,我带她看了看呕吐物,她摇了摇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到昏睡中的母亲,闻到母亲呼出的难闻气味,护士忽然有点醒悟,“哎呀,你妈妈是不是脑昏迷休克了!”,听她这样一说,我也大吃一惊,我知道这个脑昏迷的严重性的,那是生命垂危的征兆,弄不好就成植物人了,或者很快就会进入弥留。护士用指甲掐母亲的额头,看她又什么疼痛的反应没有,她又扒开母亲的上眼皮,仔细的看了看,神色相当严峻,好像一切都印证了她的判断,她说马上去跟医生反应这个问题。 护士二三分钟后,又脚步匆匆地赶了回来,向我使个眼色,“主治医生让你抓紧去一下!”我感觉大势不妙,两腿有点发慌,三步并作两步夺来到医生的办公室,那个戴眼睛的年轻女医生姓杨,说话比较和气,他是母亲的责任医师,正神色焦灼地等着我,她低低而急促地跟我交代,“真不好意思,没想到你母亲的病情又这么严重,她现在已可以确定是脑昏迷,你回想一下,她没和你们说话有多长时间了?”我说从早上到现在大体有五个小时左右,“那相当危险了,没想到病情发展得这么快,病人身体太虚弱了,真没想到。得抓紧实施抢救方案。” 医生镜片后凝重的眼神盯着我:“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可以这么说,你母亲现在已经是病危,刚才和主任已通过话了,决定实施紧急抢救方案,现在,我们就正式通知你们家属,有两种情况,或者醒来,一切向好的方面发展,或者抢救无效,那么就是人财两空,你们考虑一下。” 我问抢救需要花销多少?医生沉吟一下,说,整个费用加起来一万多块吧。你母亲的身体状况很差,即使抢救过来,预后不敢确定,不能保证能活多长时间。其实,我也跟你们家属透个实底,这种病到了这个程度,也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不能有任何的回天之术的,我们能做的只是让病情不再发展,谈不上什么治愈,她这个样子,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再出血,再昏迷,那就无法挽救了。也就是说,治疗的价值不太大,你们慎重考虑一下,你父亲年龄大了,我们也不和他商量了,我们就问你,由你决定,救与不救都在于你了,我再提醒一遍,要做好人财两空的准备。“ 此时此刻,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弟弟远在异省,妹妹也不是我的亲妹妹,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着对母亲的生杀大权,我有选择的余地么?我能担的起草菅人命的责任么?毫不犹豫的,我答应了实施抢救。 医生把一张打印的纸推到我面前,“那你就签字吧,这时候,一切都由你负责,你父亲年纪大了,钱是你们子女出,主张也由你定。签了字就没法反悔了,我还是那句话,要做好人财两空的最坏打算!”我心里惶惶的,有一种极其凄楚的冰冷的感觉,一边在合同上签字,一边语无伦次地给医生说话,“我明白母亲的病情的,她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次血,我们都有最坏打算的,即使万一有点啥,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不会怪罪你们大夫的,一切都是命,她该活多大就多大。” 医生看了看我的签字,然后把写好的处方交给护士,交代她们抓紧配药,实施紧急抢救,回来后,医生又有点伤感地对我说,“家里有啥贴近的亲戚,趁着还有口气,抓紧打电话叫来到病床前看看吧,抢救的结果还不知怎样呢!”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彻骨寒冷的深渊里,连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都不知道,医生最后的几句话很明确的暗示,母亲这次看样子是九死一生了,让亲人们赶来,见个最后一面,做人生的最后道别! 我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给妻子打电话,她遇到大事从来不慌,最有主张,这生死关头,有她在场,我才有沉重冷静的底气。妻子听说婆婆病危,立即放下煤气灶上正炒着的菜,开车往医院匆匆赶来。 我又拨通了妹妹的手机,还没说“喂”,眼眶已经湿润了,喉头也哽咽得几乎难以发声,我沙哑着嗓子通知她母亲已病危,医生已让我们做最坏的打算,让她招呼她二嫂抓紧来医院。妹妹听了我的话,也无异于晴天霹雳,她的声音也有些哽咽,匆匆答应,匆匆挂电话,开始收拾行装。 我回到病房,把父亲拉道门外,把医生的话简单转述了一遍,父亲好几分钟说出话,顿了顿,他终于缓慢地幽幽地说:“我也早看出了这个人要不行了,年前她说话就有点含糊不清的,拿东西也丢三落四的,意识有点混乱,我就有种预感,你妈这次恐怕挺不过去了。” 我看到父亲没有怎样惊慌,心里也就踏实了不少,跟他一起回病房坐在母亲的床侧,父亲趴到母亲面前,小声呼唤她几句,仍然只有污浊的呼吸,母亲眉头痛苦地皱着,表情呆板,一动不动。 护士走进来,拔掉了以前的药水,换上了急救药物,药水徐徐地节奏缓慢地灌输进母亲细弱的静脉血管。 父亲拿出冲洗干净的假牙,来到母亲侧近,“小林妈(小林是我的乳名),你张张嘴,我把假牙给你装上去,好好说话。”母亲平时是很在乎她的假牙的,装上假牙,她才能干脆利落地吃饭,说话,可是父亲把她最心爱,最需要的假牙送给她,她也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仍然纹丝不动,父亲用手掰开她的嘴巴,可是刚撬开一条缝隙,又紧紧地闭合上了,父亲苦苦地摇摇头,站在一侧,眼圈红红的,我哽咽着,低声附在母亲的耳边:“妈妈,弟弟来看你了,你睁眼瞧瞧”,弟弟拘留在外省,是母亲最大的牵挂,是她时刻思念时刻切盼的人,这个信息最能刺激她了,可是母亲还是沉沉地躺着,没有丁点动静,只有时紧时慢的默默呼吸! 父亲和我都苦着脸坐在床头,盯着沉睡得母亲,默默无语。父亲悠悠地说,要能这样走了,也省她受了不少罪,平时也不敢吃点有滋有味的东西,总怕消化不了,活着也没啥意思。父亲又压低了嗓子,神色有点恳求我的样子,“你妈要真的过去了,就用你家的面包车直接拉去火化得了,不知他大嫂能同意不?”我说,能行的,自己家的老人,也没什么可嫌弃的,我们生怕母亲听见似的,又挪得离母亲远一点,继续小声商议,我说弟弟不在家,我也不想大操大办,后事简单低调点吧,父亲说,嗯,要是简单操办得话,估计最多两万元铺底也就够了,我说到时候我挪挪借借还是来得了的。父亲听我如此一说,表情放松了不少。 望着纹丝不动的母亲,我和父亲面面相觑。缓了缓神,我想起医生叮嘱的要让亲人来见一见,就跟父亲商量联系哪些亲人,父亲把手机递给我,“这里面有你四姨,五姨的电话,你跟她们说一声,你二舅那面,你四姨会联系的。” 我接过手机,来到病房大楼的门西侧,蹲在台阶那儿拨通了四姨的手机,哽咽着告诉她我妈在医院,医生已宣布病危。四姨听了,好像也没太出乎意外,她说年前到我家来过,看到我妈已虚弱不堪,风一吹就能倒的样子,也感觉她不长久了,这次病危也在情理之中。 我说医生现在正尽力抢救,看看有没有还阳的的指望。四姨马上说“大外甥呀,四姨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妈到这种程度了,不救也罢,我们这些亲戚不会有任何责怪的。救过来也没啥大活头了,多活十天半个月,有什么意思,她也不能帮你们什么忙,况且她自己也遭罪呢。少花也得万儿八千的,你们年轻人日子还得过呀,不能把钱都砸到这个无底洞里。我知道你们弟兄手头都不宽裕,这些年,你身体也不好,难处多呀。本来你弟弟还能能蹿能蹦的,一冲一挡还行,偏偏又进去了,你说事情就这样的堵心。我找算命先生给你弟弟算过命了,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得等到四五月份。现在,这担子都落到你一个人头上了,我真不忍心看着你们花这个冤枉钱呀。” 我咬着牙说,“四姨,你放心,我们就是借钱也得抢救我妈。四姨,如果我妈真的过去了,我想就用我家的面包车拉到火葬场火化了,也能省点。四姨马上制止了我:“外甥,不能这样做!一定要在你妈有口气时把她拉回家,活着占着两间房,我们邻居有个老人在医院里断的气,没占到祖房,埋怨可大了。你妈如果还是昏迷不醒的话,你就抓紧让你媳妇把她拉回老家,临死前一定要占上两间屋子。”四姨的主张是显而易见的,她甚至愿意让我们现在就放弃治疗,把母亲拉回老家,好占着两间屋子!我们虽然不迷信,但是也不能违背这些老人家的心愿。我马上保证,现在先尽力抢救着,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我妈明早还是一直昏迷不醒,我就把他拉回老家,如果这期间,上天保佑,她能醒过来,就接着继续治疗。有了我这番的慷慨陈词,四姨这才放心地挂了电话,答应明上午过来探望。 望着蜷缩在病床上无声无息骨瘦如柴的母亲,我感慨颇多。我的大舅大姨三舅都先于她而走了,她凭着病弱之躯能硬撑着活到今天,相当不容易了,也都多亏了父亲的细心照料,几次三番的折腾,病重,让父亲担惊受怕,疲惫不堪,或许母亲的这次离去,对父亲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没有母亲的拖累,或许更能长寿些。 想起母亲这辈子,在我的记忆中,不识字的她,性格略有些烦躁易怒,干活劳累啦,家里缺钱啦,总能听到她的吵吵嚷嚷,满腹牢骚,少年时,当我求学时,为交那十块二十的学费,或者三五块的伙食费,总要挨她的嘟囔“上什么上!能有什么大出息,下来干活还能省点。”然后,是父亲对她语重心长的开导,温婉的劝解,之后,我才能拿到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带着母亲汗水淋漓赶烙出来的煎饼,还有自己动手炒的盐煮黄豆,去临镇的学校求学。 那时,祖父已七十多岁了,在伯父家和我家五天一轮换的供养,祖父头脑有时会短路,说话有时很冲,平时好喝一两盅酒,母亲总抱怨这点,“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喝什么酒呀,哪有闲钱买呀。”然而只是口头上的抱怨,最终依然每天中午晚上的两顿酒供着祖父,等祖父轮到我家吃饭时,母亲有时还特意的炒点鸡蛋啥的,给他老人家下酒,这在当时的拮据家境中,已是不可多得的了,祖父即使有点头脑糊涂,也能感觉到我母亲的刀子嘴,豆腐心。 八十年代中期,刚刚分单干,我们家族较近的几家组成了互助组,大人们冲锋陷阵,农忙时连顿饭都吃不完整,母亲的农活干的虽不算太利落,但伙在一起,从没落下过什么重活累活,虽然干的略有些吃力,但也顽强的撑了下来,小家庭,没有什么别的额外收入,全靠种点庄稼,供养我们兄妹三个,也算相当不容易了,即使没能像别人家那样,翻盖起高大的瓦屋楼房,我们在父母的照顾下,没病没灾的健康长大,也算知足了。 五十岁前后,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由于没拿当回事,或者因为手头总不宽裕,没及时狠治,一直不能根除,随着年龄日增,病情也在加重,在别人看来,老夫妇俩住在二儿子宽敞的大房子里,儿媳妇从没跟他们红过脸,逢年过节的都像亲戚一样的回家团聚,应算是很幸福祥和的了。岁月的老去,儿女分家独立之后,只有二老相互搀扶着过日,父亲是个很能忍让的脾气温和的人,没有了复杂的大笔花销和各种纠纷,渐渐的,母亲的脾气也转好了许多,言辞也不像壮年时那样的呛人了。阅历的积累,生活的安定,使得她心态平和,处事圆滑了许多,在庄邻儿女面前完全是一个面慈心善的老太太形象,大家彼此互相谦让,维护着难得的和谐亲情。 我又想到,一旦母亲去世,父亲少了说话的伴儿,会有些失落孤单,70多岁了,也不能再出去干过重的体力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守着几间大房子,早早晚晚独自摸索着,他身体还较硬朗,剩下几十年怎么过?我的脑子里纠结着,烦乱着,甚至有时一片麻木和空白。 这时妻子匆匆的推门进来,关切地来到病榻前,俯下身子观察沉沉昏睡的母亲,父亲凑到母亲的耳朵边“小林妈,你大儿媳妇来张望你了,睁眼看看呀。”徒劳的呼唤,母亲毫无反应。我们三个人对视了一下,都无奈地摇头。眼眶涩涩的。我向妻子介绍了母亲的病情,把母亲咖啡色的呕吐物端给她看,妻子沉思了一会,说,那咖啡色的液体是不是血液呀?是不是老人家的血都流尽了,稀释成了褐色?这样就彻底没治了。你们看看,她腿上的皮肤哪还有点红气呀。听到妻子这样的论断,我的心更冷到冰点,母亲真的没有还阳的可能了?这就是她最后的末日?我的思维一片空旷,焦躁,绝望,疲劳,编制成一顶重重的大帽子,罩在我的头上,太阳穴剧烈的跳动,像要炸裂开,平静躺着的母亲在我的泪光中模糊虚幻起来。 妻子相对还是比较冷静的,她先同我父亲聊了会,了解母亲发病的过程,顺便也附带着安慰父亲,让他不要太悲伤,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接着,妻子又跑去医生办公室,询问治疗方案,回来后,神情也挺忧郁的,看样子真是无计可施了。她跟我小声的商讨,医生说清醒过来的几率还是有的,就看病人的身体状况,有时病人的意志也很重要的。什么意志,母亲都昏迷成这个样子了,哪有毅力自我控制呀,听天由命罢了。妻子把我拉到门外,小声告诉我,医生让我们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前有类似的昏迷病例,从家里往医院送,没到半路患者就咽气了。我叹口气说,也有准备的,都这么多年了,总得有解脱的一天。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小妹和她二嫂过来了,我急忙出去迎她们,到了门口,看到她们各抱着自己岁把的孩子,拎着包,随着我顺走廊道进来,看到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妹妹的眼窝也湿润了,父亲俯下身子,徒然地告诉母亲:“小林妈,你闺女和二儿媳妇来了,你大外孙子和小孙女都来看你了,睁眼看看呀。”母亲皱巴巴的黑瘦的脸毫无变化,只有胸脯还稍起伏着,维系着仅有的呼吸。她的昏迷把我们这些周围的亲属带入了万劫不复的谷底,弟媳妇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连小侄女递给她的凳子也没心思坐了。 我强忍着绝望和悲伤,询问弟弟的事情处理怎样了,询问妹妹家的另两个孩子托付给谁照管了,她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眼光时不时凄楚地瞟向病床上的母亲,希冀能有一点点的转机。 我拿过手机,找到堂弟的手机号码,一个人人溜到门口和他通话,正好,大姑家的三表哥听说祖坟树碑了,今天带大姑来祭祖,正在堂弟那儿喝酒吃饭呢。听到母亲的不幸消息,他们弟兄说先要把大姑送回家,然后过个把小时开车赶来。我听说三表哥喝了不少酒,再三劝阻他别酒驾了,然而他很坚决地说要来,然后挂断了电话。 父吊针瓶离的药水要滴尽了,父亲出去找护士换水,可是他竟然去推卫生间的门,虽然他向我们说,自己能挺住的,可是猝然而至的恐怖,过度的悲哀,让他一时竟转向了,妻子马上注意到了,让我带父亲出去。我一边走,一边安慰父亲不要太难过,人生总要走这一关的。父亲点头答应着,可是明显的心不在焉,我此时又能说什么呢?任何的安慰对他老人家来说都没有多大意义了。事到临头,谁又能沉得住气,谁又能极端的冷静理智呢? 换上了新的吊瓶,药水缓缓滴往母亲静脉种渗进,时间到了下午一点半左右,在药水单调的低落中,在我们的无望喝默默祈祷中,母亲忽然动了动身子,左右晃了晃头,一直盯着她的父亲马上脸现惊喜,“小林妈,你醒了吗?”母亲的眼皮费力地动了动,可还是非常疲劳,睁不开来,父亲高兴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和在坐的每个亲人交换着喜悦的眼神,我也俯下身子,想尽办法唤醒母亲“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的话,你就点点头。”母亲的下颌轻微的象征性的往下沉了两沉,向我们示意着。行了,母亲已有意识了!我的热泪涌到了眼里,奇迹终于发生了!随着吊水瓶内的液面一点点的降低,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越燃越亮! 妹妹走到母亲的头侧,俯下身子“妈,我是灵芝,我来看你了,还有你外孙子鸿昌,你能听出是我吗?”“你是灵――芝-……”,母亲的嘴里能含糊出这样的字眼了。虽然她的眼睛始终还不能睁开,但是,她的话语给了我们无比的振奋。 我来到医生的办公室,向医生报喜,感谢她的及时治疗抢救。医生的眼中有了很大的欣慰,然而,又郑重的说,这也只是个临时的好转,至于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没有把握,你们家属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的。药还是照个方子用,但是我跟你说下,这个药是我们医院仅有的两支,一下午就用完了,你傍晚到县城的各大药房问问,看有没有类似的药水。如果没有的话,你得去市区的医院去打听,那儿应该有,即使不是一模一样的,也有替代品。“我答应着,让医生把药水名字写给我。然后一边感谢着,一边回病房。 我把母亲苏醒的情况电话告诉了四姨,让她不用过分担心了,明天不也不劳她来了。四姨说明天会约同五姨一起来的。我也只好答应。然后,我又告诉三表哥,让他不用费心了,他说已经开车在路上了,很快就到。我就到外面停车场上去迎他们。 在广场上,我望向蓝色的天空,看到那朵朵白云,自东向西悠悠翻滚着,压抑已久的心情终于得以释放。母亲活过来了,终于还能在这片天空下还能自由地呼吸,这是她的幸运,也是我们儿女的福气。这时,我脑际响起了强劲有力的女声“many nights we'are pray.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and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we were moving mountains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 you can achieve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u will when you believe in this time of fear.when prayer so often proves in vainhope seems like the summer birds. too swiftly flown awayand now i am standing here.my heart's so full i can't explain.心seeking faith amp; speaking words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when you believe)! ……………… 然而,第二天,当我回家吃饭,从网上却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亿万人无比崇拜的那个美国歌星,那个唱响《当你相信》,唱响《保镖》的惠特妮休斯顿,竟然在母亲不省人事的那一天,为参加格莱美大奖,在酒店里离奇猝死!时年仅49岁。惠特尼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个她无比留恋的人间,她的是是非非传奇的一生,终于划上了完整的句号。虽然,我的母亲神奇复活了,但是,我的心却为惠特尼的过世,而再度陷入极度的悲凉。愿这位伟大的女歌星能早升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