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文章
-
像风一样离去
(11-05-10 04:53)【编者按】我象风一样的回到村庄,几天后,又被那阵风刮走,留下一个绵长的影子……作者从回村的见闻中,感觉到这些年在城市里的生活,卑微得甚至不如一株草。作者在不经意的叙写中,流露出欣喜与淡淡的无奈,不管身在何方,它们始终在游子的心里,于是表达出:离开村庄,村庄便停止了生长。村庄记住的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我记住的是我离开时村庄的模样,我们都在时间的某个角落等待着对方。
我回到村庄的时候,村庄正在刮一场西南风。和当年我离开村庄时刮的那场风正好相反。
风不大,只是吹起一些尘土,一些落叶,一些小孩吃完方便面扔在村庄里的塑料袋。空气中到处飘浮着些轻巧的东西。我进入村庄的时候,村庄空荡荡的。狗没有叫,大约那些狗正好是好多年前村庄里的狗,它们熟悉村庄里每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一刻,它们听见的是好多年前就行走在村庄里的脚步声。鸡也没有叫,鸡对村庄里的事情反应迟钝而漠不关心。它根本不会去揣测村庄里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会对它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它根本无法判断你是谁,即使一个从未在村庄出现过的陌生人走到它的身边,它也懒得瞅你几眼。鸡的世界是一个悠闲而超然的世界,它可能比人活得更满足更清醒。
正值中午,村庄里静悄悄地。人们都伏在地里劳作,庄稼已经长得足够淹没他们的身体。他们没有觉察到空气中多了一个人的呼吸。其实,打我进入村庄的时候,就扰乱了村庄里空气先前的布局。我在一棵老松树下歇息了一阵子,我吸走了那里好多年没有动过的空气。周围的空气迅速向老松树下流去,填补被我吸走的部分。我又爬上多年前我爬过的一棵板栗树,我站在树上试图把藏在庄稼地里的人找出来,可是我没有发现一个人。风把树枝荡得东摇西晃,树枝也胡乱地捣鼓着空气。我在树上摇晃了一阵子,又重新回到了地面。
走到屋后头坪里,我遇到了文轩的爹。文轩的爹正躬着背在地里薅草。我看了他好大半天,他都没有察觉。他还是十多年前的样子,头上裹着一个黑头巾,上身穿的是一件蓝色涤卡的对襟衣衫。事实上,打我记事起,他就是那个样子,就好像这些年他停止在时间里了一样。
“伯,您正忙着呢?”
文轩的爹直起身子,从苞谷林里冒出半个头来,他瞟了我一眼,复又埋下头去忙活。大约他已不认得我了。
“伯,您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变呢。”我继续招呼道。
文轩的爹愣了一下,又一次将脑袋从苞谷林探出来。他干咳了两声,问了句:“您这是要到哪里去?”
我差点笑出声来。“伯,您瞧瞧,我是哪个?”
文轩的爹用浑浊的目光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好几遍,说“您像一个人。”
我问道:“谁?”
文轩的爹说出了我爹的名字。我终于笑出了声。我说:“伯,我是斌娃。”
“斌娃?真是斌娃!好易得晃(方言,时间过得真快的意思)啊,一眨眼就这么大了。”伯从苞谷林里走出来,把手在胳肢窝了擦了又擦,然后从一大蔸草里拿出一个大瓷缸,瓷缸上倒扣着一个茶杯。我知道,瓷缸里是熬好的红茶。
伯给我倒了一杯说:“茶太苦,你喝不惯罗?”“还好呢,伯。”伯就嘿嘿地笑。接过伯递来的茶,我看见了一双粗糙的手,一双满是老茧、满是泥垢的手。在村庄里,任何一个靠泥土生活的人,都有一双这样的手。如果村庄里有哪个人的手细皮嫩肉,那肯定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这样的人在村庄里被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是要被人唾弃和不齿的。
伯又给自己倒了茶,喝了好几杯,喉结一上一下,声音极响,甚是快意。喝完茶,伯扯过一把旱荷叶,往地上一垫,一屁股坐了下去。我蹲在旁边,我已经不太习惯这样的坐姿,我怕脏了我的裤子。
我们的交谈很随意,大多数时间是伯在询问我外面的事情。我尽可能地给伯勾勒一个完整的村庄外的世界。对于村庄外的事情,伯是一个陌生者,同时又是一个好奇者和羡慕者。后来,伯给我说了一些村庄里的事情。讲述村庄里的事情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倾听者。我发现我成了村庄的陌生人。我好像在倾听一个与我无关的村庄的遥远的故事。而我也确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亲近过村庄,没有看过村庄里的花草,没有爬过村庄里的树,没有走过村庄里的路,没有呼吸过村庄里的空气,没有倾听过村庄里的声音了。
伯的讲述最终回溯到我离开村庄的那会儿。事实上,伯对我的记忆,还停留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他比我自己更了解那时的我。至此,村庄里出现了我的身影,庄子里的事情也才与我有关。我和伯又寒暄了一阵子,伯还饶有兴致地讲起我穿着开裆裤在满村庄里瞎跑的事,逗得我哈哈大笑。
告别伯,太阳只有两杨树高了。
回到家,院子里空空的,院门用一根木棍顶着。我轻轻地叫了几声爹娘,没有人应答。他们一定是在哪块地里劳作。我没有大声喊叫。如果我大声叫喊的话,会惊扰大半个村子的。
我随手拾了一根树枝从门缝里把顶门的木棍拨开,刚好起了一阵风,把门给刮开了,我趁机就溜进了院子。狗在西墙根晒太阳,我一进门就向我冲来。在距我不到一尺远的地方,狗突然跃起,前爪往我胸前一搭。我一时没有站稳,就给撂倒了。狗摁着我,舌头不断地舔吮我的脸,痒得我笑出了声。我求了几声饶,试图站起来,又被它按倒了。我索性绊倒狗,和它在地上打起了滚。过了两三分钟的光景,狗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大约是没有闹尽兴。我有些累了,决定拿出人的尊严,呵斥了它几声,它这才看着我悻悻地离开。我望着它笑了一下,它立刻又想靠上来。我只好重新垮下脸来。南墙根的一群鸡显然已经忘了我,它们耷拉着眼皮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两眼,没有丝毫的激动。
火坑前的板壁上仍然挂着一些薅锄、镰刀;厢房前的板壁上则挂着一些满蔷。我知道,其中有一件是属于我的。但我离开村庄已经好多年了,它们也被荒芜了好多年。
我又到茅厕里去撒了一泡尿。年猪就喂在厕所旁边的圈里。我一打开厕所的门,猪就从窝里钻了出来,它们翘起长长的嘴巴对着我就是一阵哼哼哈哈。我没闹明白它们什么意思。尿一撒完就急忙离开了。
我走出院子,又四下里转了转,最后断定爹娘在湾里劳作。
我到湾里接爹娘的时候,正碰到爹娘收工回来。看到我,爹娘很激动。娘说我也不给家里招呼一声,爹好去接我。我说想给娘一个惊喜,娘就笑了。娘总有问不完的问题:路上顺不顺利,饿了没有,什么时候动身的。看见我满身上是泥,娘又急忙问我是不是摔跤了。
我要接过娘的背篓,娘怕弄脏我的衣服。我说,不是已经很脏了么。娘没有说话,又笑了。
踏进院门的时候,太阳就落山了。爹忙着给年猪喂食,娘忙着做饭,而我则和狗一起,把鸡关进笼子里。
我和爹又聊了一会儿工作的事,娘就叫我们吃饭了。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了。
我去寻了很多花,找了很多树,爬了很多路。我要让他们重新熟悉我,认识我,更新我在他们记忆中的形象。
很多花开了又落了,很多树壮实高大了。那一丛野百合还在,而且在它的周围又冒出了若干新的百合。但有一片蝴花走失了。我没有离开村庄的时候,这里有一大片蝴花。一到夏天,蝴花开得赤黄赤黄地,金灿灿耀眼,但现在它们已经被茂盛的旱荷叶替代了。当年被我跨越而过的那棵桦古树,已经长得老高。我只能以仰望的姿势,询问它这么多年村庄里的变化。
我放牛时踩出的几条道已经荒弃了。如今,它芳草蔓蔓。拨开茂盛的野草,是一层陈腐的枯枝落叶,显然,已经好多年没有人行走了。我凭着记忆在路上行走,在杂草丛生的枯枝败叶中体验曾经赶着牛踏在路上的感觉。这种感觉遥远而陌生;有风拂过,一阵牛臊味依稀传来,顿觉清凉而实在。
早晨经过牛圈时,满圈牛铃声盈耳。我打开圈门,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忘记了,好多年前,牛就卖了。
那头牛在我家生活了六七年。一年冬天,它突然挑食起来,不肯吃草。一个冬天下来,就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爹整天叨念着这事,说不肯吃草只有卖掉。没想到来年春天,它又是一阵疯长。可是在那个正要犁地耕田的季节,牛又瘦了下来。庄稼人最担心的就是错过时节,错过时节就意味着饿肚子。爹又叨念着卖牛的事。牛最终卖给了牛贩子。卖牛的那天,牛赖在圈里死活不出来,是贩子用棍条抽出来的。牛被牵走的时候,不止地流泪,娘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一条离开村庄的牛,是悲哀的。不知道牛有没有想过,它原本是应该在村庄里老死的。可现在,它早已被分解成一块块牛肉,进入了千家万户,进入了很多人的胃里,然后被分解、消化,最后在这个世界灰飞烟灭。
我试图在路旁找到一些我当年留下的痕迹,比如,挖的一个蓄水坑,或者是一方和伙伴杀棋的石头,或者某个石头缝里藏的抓子用的石子。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坑已经平了,石头不见了,石子也消失了。我离开村庄这么多年,路就失去了这么多东西。这到底是路的损失还是我的损失呢!我一时想不清楚。
我看见了一片长势茂盛的茅草,它们已经漫过了我的头顶。茅草是牛最喜欢吃的东西。我拨开草兜看了看,没有短桩,只有枯死的草茎。显然,这一片草已经躲过牛和割草人好多年了。在这样一个清净的野外,恣意地生长,走完了一个又一个平凡而完整的生命流程。我想,草是幸福的。
这些年,我在城市里卑微地生活,我甚至不如一株草。草不会像我,到处游荡;也不会像我在村庄里活着弄不出什么名堂就拔腿离开村庄。它们把生命深深地藏在了厚厚的黄土里,不论贫瘠还是荒凉,它们都在耐心地等待来年的那一缕春光。
我还遇到了一群狗。
它们好象要去处理一件很隐秘的事情,怕村里人知道,所以它们没有选择村庄里的大路,而是选择了这条被遗弃的荒芜的路。
有几只老黄狗是好多年前村庄里的狗,见到我,它们很自然地侧身站在路边给我让路。我忽地内疚起来。因为领头的那只狗曾被我用石头扔过,拖着一条瘸腿,在村庄里颠簸过好久。那是昌国家的狗,一头很凶猛的狗。
在村庄里,难得出一条厉害的狗。昌国家的狗是打败了半个村庄里的狗才当上狗王的。当上狗王后,整天耀武扬威地纠缠我们家的花母狗。国昌曾经捣过我家槐树上的鸟窝,我叫他不要捣,他偏要捣,所以我就用石头扔他家的狗。狗再厉害,它还是一条狗。所以,狗王被我用石头扔了后,见我就低着个头躲躲闪闪地。不过狗王最终还是和我家的花母狗繁衍了一窝活蹦乱跳的狗仔。这么多年过去了,狗也老了,但它仍是村庄里的狗王。
我认出了它,不知它认出我没有。
还有几只年轻的狗,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们。它们是在我离开村庄后进入村庄的。其中的两只用陌生的眼神望了我两眼,然后,面向天空胡乱嚷了两句。我没有理会它们。我知道,它们不会咬我。
我刚挫过身,狗又上了路,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我又胡乱地在山林里窜了一阵子,直到娘叫我回去吃饭。
接下来的几天,村庄里没有刮风,一丝柔弱的风也没有。以往风大的时候,一刮风我就能听见村庄里远远近近的各种声音。
风是一个顽皮的家伙,它会把村东头的某个鳏夫的嘴刮到村西头某个寡妇的家里;也会把村西头某个女人晾晒在院子里的内裤刮到村东头某个男人的炕头。耍得兴起,它还会突然把深夜中一对年轻夫妇的摇床声,散播到村庄的每个角落,扰得一些没有睡着的发情的狗,在窝里团团转圈。
一个星期后,我又要离开村庄,回到那个留不下我任何足迹的城市,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离开的时候,村庄里照例刮着风。我被那阵风刮走,留下一个绵长的影子。就像村口的那棵老树一样,太阳经常把它的影子拽到村外。但我知道,太阳一松手,树影拉得再长也会弹回村庄。离开村庄,村庄里就少了一个说话的人。有一些事也因此随风而去,不再被人提起。离开村庄,村庄便停止了生长。村庄记住的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我记住的是我离开时村庄的模样,我们都在时间的某个角落等待着对方。
来年村庄刮一场相反方向的风的时候,我又会刮回村庄,我和村庄重又回到同一的时间里,伴随着一些陈年旧事,再一次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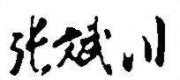






一共有 4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