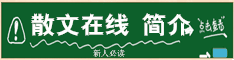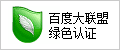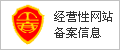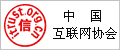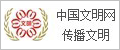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3、喝茶 读徐志摩先生会见哈代记,中间有一句道:“老头真刻啬,连茶都不教人喝一盏……” 这话我知道徐先生是在开玩笑,因他在外国甚久,应知外国人宾主初次相见,没有请喝茶的 习惯。 西人喝茶是当咖啡的,一天不过一次的,或于饭后,或于午倦的时候,余是口渴,仅饮 气蒸冷水,不像中国人将壶泡着茶整天喝它,他们初次见面,谈话而已,也不像中国人定要 仆人捧出两杯茶来,才算敬客之道。这是中西习惯不同之处,无所谓优劣,我所联带要说 的,是外国人对于应酬的经济。 我仅到过法国,来讲一点法国人的应酬罢,法人禀受高庐民族遗风,对于“款客之道” Hospitalite素来注重,但他们的应酬,都是经过艺术化的,以情趣为主,物质 为轻,平常酬酢,不必花费什么钱财,而能尽实际之乐。 中国人朋友相见不久,便要请上馆子吃饭,法人以请吃饭为大事,非至亲好友,不大举 行,而且也不大上馆子,家中日常蔬菜外添设一两样便算请了客。至于普通请客,就是“喝 茶Ptendreauthe了。每次茶点之费不过合华币一元,然而可同时请四五客。 初交不请,一定要等相见三四次,友谊渐熟之后再请。他们无论男女自小养成一种口才,对 客之际,清言娓娓,诙谐杂出,或纵谈文艺,或叙述故事,或玩弄乐器,或披阅名画,口讲 指画,兴会淋漓,令人乐而忘倦,其关于国家社会不得意的问题,从不在这个时候提起。他 们应酬的宗旨,本要使客尽欢,若弄得满座欷s[,有何趣味呢? 法人无故不送人礼物,送亦不过鲜花一束,新书一卷而已,而且亦必有往有来,藉以互 酬雅意。中国人不知他们习惯,每每以贵重礼物相送,不但不能结好,反而引猜嫌。我有一 个同学,他有一个法友,是书铺的主人,平日代他搜罗旧书,或报告新出版著作的消息,甚 为尽心,这位同学便送他一个中国古瓷花瓶,谁知竟将他弄得大不自在了,以后相见虽照常 亲热,而神宇之间,颇为勉强,则因为他们素不讲究送礼,忽见人送值钱的东西,便疑心人 将大有求于他的缘故。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亲朋的往来,有之则应酬原所不免,但应酬本旨在增加交际间的乐 趣,使人快乐,也要使自己快乐;若为应酬而弄得财力两亏,疲于奔命,那就大大的无谓 了。 中国是以应酬为最重要的国家,而百分之九十九的应酬都是无谓。朋友虽无真实的感 情,亦必以酒肉相征逐,婚丧呀,做寿呀,生日呀,小孩出世呀,初次见面呀,礼物绝不可 少,而以政界应酬为最多。我有一个本家在北京做官,每年薪俸不过二千余元,而应酬要占 去八九百元。虽说我送了人家的礼,人家也送我的礼,但现钱可以买各项东西,礼物不能变 出现钱来。这种应酬,等于拿金钱互相抛掷,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而在应酬太繁,不能维持 生活,不免要于正当收入之外想其他方法,中国官吏寡廉鲜耻,祸国殃民之种种,不能说与 应酬无关。 选自《苏绿漪创作选》,1936年上海新兴书店出版 4、我的教书生活 我因为出生于旧时代,又出生于过分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尊长们认为女孩儿认识得几个 字就算不错,进什么学校,靠她将来赚钱养家?还是靠她为官作宦,荣宗耀祖?后来亏得我 自己拚命力争,家里才让我进了安徽省城的第一女子师范。进师范学校的好处是不须缴学膳 费,连穿的制服,用的书籍,都由公家供给,那时我家经济状况非常窘迫,念书的男孩子又 多,我们想进学校,只好进那不花钱的了。初级师范卒业后,在母校服务二年,又进了北京 高级女子师范。帅范学校以造就学校行政人员及各科教员为宗旨,我既受了双料的师范教 育,当然决定了我一辈子当教书匠的命运。 把自己教书年月屈指计算一下,从小学起,历中学、大学,一共经过了四十余年,单以 大专论也有了四十年,真算得一个不折不扣的“教书匠”了。 关于我教小学的掌故,在归鸿集《教师节谈往事》一文中叙述得相当详细。于今台湾教 育界产生了“恶补”这个名词,我在民六年初级师范卒业被留母校附小服务,便曾干过这个 玩意。是否戕贼了若干儿童身心我不知道,但自己健康却受了绝大的影响,升学女高师和留 学法国的前后六年里我始终在病魔指爪下讨生活,虽然没有病倒床上,但恹恹不振的身体, 限制了我奋勉的用功,从而也限制我后来的成就。可算是我一生最大遗憾的事。不过目前台 湾教师替学生恶补,目标在于猎取金钱,而我则受着盲目的献身教育热忱策动而已。以良心 论,我是平安的。 民国十四年,我自法邦辍学返国,奉母命与南昌张宝龄结婚,外子时在苏州东吴大学授 课,我们在苏州组织了小家庭。从前北京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有?δ鞘币苍诙*大作短 期的讲学。他因要回南京金陵女大,介绍我代替他的课,同时又荐我为景海女子师范的国文 主任。我对陈师说,我过去仅教过小学,在母校也兼过几小时的课,那只是预科,程度比高 小差不多,一下子叫我教大学,如何能胜任呢?陈师说,你不必发愁,这一班学生是我教 的,性情都很温良,决不会同你捣乱。况且你正式名义是在景海,东吴不过兼课性质,学校 与同学对你都不会苛求,你只须自己多预备,便足以对付了。我在东大每周兼课六小时,教 的课程是诗词,上课也没有一定的教材,一会儿是几首唐诗,一会儿是几首宋词。学生中有 一位谢幼伟君,广东籍,为人非常忠恳。受了陈师的嘱托,对我照拂无微不至。他后来赴美 学习哲学,著作甚多,成为学术界名流,对我至今仍以师礼相待,这固是谢先生的厚道,但 实使我惭愧。 这种拉到什么教材随便就教的游击教法,是陈师遗下的。教者是感觉吃力一些,但学者 的兴趣却因而浓厚。记得我们有一回谈到李义山的无题诗,学生要求选几首为例。我选了几 首,同时又选了几首有题等于无题的《碧城》、《玉山》、《圣女祠》,更选了那聚讼纷如 的《锦瑟》,为了注解,自东大图书馆借出冯浩、朱长孺、朱鹤龄等的注本来看。看了之后 恍然若有所得,于是对学生说,李义山的无题并不是托夫妇以言君臣,也不是故意以可解及 不可解之词,文其浅陋,它是有内容的。这内容是什么,我已看出一点子了。请你们假我以 月余之力,将义山诗注看完,然后再与大家讨论,于今且找点别的材料来教吧。 月余之后,我已确定义山与女道士及宫嫔恋爱的关系,将义山集中这两类诗各提出若干 首对学生讲解。谢幼伟先生的好友张鹤群君首先赞同我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李 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在东吴大学廿五周年纪念会刊行的《回溯》里发表,对于宫 嫔事则班上同学都表示怀疑。因为中国君主时代宫禁异常森严,唐代宫闱即说不肃,也决无 容许外面男子混进之理。我不管他们的意见,还是照我所发现的路线摸索下去,等到寒假到 来,将所得资料整理成篇,成了六万字左右的小书一册,题曰《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证》付上 海北新书局出版。十余年后改名《玉溪诗谜》归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今。 现收《蠧鱼集》的《清代两大词人恋史研究》也是东吴大学教课时与学生偶然谈论引起 来的。第一次是讲纳兰容若的词,张鹤群君送了我一部精刻的《饮水词集》,比一般通行本 所收词较多,并附容若的诗。我忽然想到红楼梦内容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此书系指康 熙朝权相明珠家事,贾宝玉即是纳兰容若,我读容若词,果然发现容若少时恋一工愁善病林 黛玉型的女子。此女子自幼居相府中,与容若关系似乎非姑表兄妹则为姨表兄妹。后此女被 选入宫,容若以身为帝王侍卫,尚与相见数次。女郁郁死,容若悼念终身,饮水集中所有哀 情之词均为彼姝而作。清代某笔记曾记其事,指为红楼故事的根本,我读了饮水词,觉其说 不无可以成立的理由,写了一篇文章,以饮水词情词逐一与红楼梦对勘。此文即名为《饮水 词与红楼梦》。 第二个清代大词人是顾太清,相传她与当时名士龚定庵有过一段罗曼史,曾孟朴先生的 孽海花曾有详记,冒鹤亭氏又有丁香花诗的附会。孟心史撰《丁香花疑案》万余言,力辟其 诬。我和东大学生谈论,曾说这件疑案值得再探讨一下,学生赞成。有一位家中藏书甚富, 居然借给我一部木版的《东海渔歌》,还有几种太清夫妇的作品。我开始研读,茫然莫得头 绪,遂又弄了一部龚定庵集,读了定庵的《无着词》以后,我本来想替顾太清辩诬的,这一 回意见改变了,竟想附和曾孟朴、冒鹤亭的意见,以为龚顾恋史是真确存在的了。先是,我 在上海认识袁昌英、杨端六,因而也认识他们朋友王世杰校长,武大文学院有个学术季刊, 王写信征文于我。我将《清代两大词人恋史研究》的第一篇《饮水词与红楼梦》寄去,已在 季刊上发表了,季刊编辑又写信来讨下篇。在引论里,我固说我是拥护孟心史的,现在我的 答案似乎要落在否定方面,这叫我如何自圆其说呢?虽说学术之事以服从真理为第一,发现 自己的错误,应有承认的勇气,不过问题尚未着手探讨,便先宣布结果,后来又要悔那脚 棋,究竟是可笑的。 我正在自怨孟浪之际,忽于无着词发现一中罅隙,那便是定庵外舅段玉裁替无着词所撰 序文的年月日再把龚顾年龄一考查,定庵写这些词时,顾太清尚仅是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六 岁女孩居然能与人谈恋爱,非“人妖”莫属,而顾太清却是个正常的女人。于是站在孟心史 同一观点的《丁香花疑案再辩》撰写成功了。当然,我这篇《丁香花疑案再辩》与孟心史并 不曾说同样的话,他的论点不甚坚强,而我的“倒溯上去,年月不合”却可替顾太清洗刷。 恢复她的清白。我后来把这一篇寄给曾孟朴先生,他原已在他的真美善书店替我出版了一本 《蠧鱼生活》,内有我《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及一些小考据。我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证》他也曾读过。至此,竟誉我为学术界的福尔摩斯,说我天生一双炯眼,惯于索隐钩深, 解决他人所不能解决的疑案。实际上,我比较引为得意者,还是我后来的屈赋新探,这不仅 关联着屈原作品问题,还关联着中国文化来源问题,并牵涉全世界文化彼此影响的问题,关 系之大,无以复加,可惜孟朴先生已不及见了。 我在景海女师当国文系主任,以聘请教师未得其人,我竟又表现出教安庆女师附小时的 傻劲,自己教了两班国文。每班学生五十余人,两班在一百以上。那时候作文是每两周一 次。我每周上课十八小时,还要批改百多本作文簿。教国文,有现成的国文教科书,买了教 案来,只须照本宣扬,循序而进就是,并不耗费我多少时间。批改作文却麻烦。我原来自安 庆那个文化落后,科举余毒未尽的初级女子师范,我的国文教师,在前清都有功名,非举 人,则拔贡,他们从前都曾在所谓“闱墨”上用过功夫。替我们批改作文时,浓圈密点,淋 漓尽致,总批之外,尚有眉批,旁批。那些批语说夸诞,是够夸诞,说美丽,也够美丽。一 篇改文托在手里往往令人看得心花怒放,真当得起“艺术化”三个字。可惜这种艺术,鼓励 学生上进作用小,煽动学生虚荣心害处却大。我在苏州教书时虽已在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旧 时的习惯一时如何改得了?对于批改学生作文,我也想把老师的那一套,如法炮制起来。但 老师那一套经过多年修炼功夫,以我微末道行,怎样学得像?只能学到一点皮毛罢了。可 是,这点皮毛也就苦了我。我常常为思索一个批语,要费去比改一篇作文两倍的时间。每改 一期作文,总要弄到十二点钟以后,始能就寝。前文说过,我自升学女高师及留学法国的那 几年内,健康一直很坏。回国结婚后,又加以严重的贫血,常闹头昏,心跳、腰背酸痛,医 治过几次,没有效果,也就懒得再理会了,不过那时候我正当春秋鼎盛之际,教书的辛苦, 竟能撑持下来。 民国十六年,外子返沪,我们又自苏州搬回。次年,经人介绍我到沪江大学教书,仅教 一年便离开。这一年中并无足记的事件。但认识顾实先生却算我记忆中一枚发着光彩的石 子。顾先生面目黧黑,身躯肥胖,蓄着胡子,经常穿一袭布质长衫,拖一双布鞋。说话同他 文章一样,有大言炎炎,不可一世之概。我说这话并不是说顾先生像目前一些恬不知耻自吹 自捧的青年一般,他倒很像个中国读书人,学问虽甚渊博,却并不借此向人炫露。他所过分 夸张的却是中国文化的优越与伟大。他以为在两河、埃及、希腊、印度几支古文化里,中国 的应当坐第一把椅子。那时他的《穆天子传讲疏》尚未撰写成就,但他却已做了不少准备工 作了。沪大中文系同学举行小型学术讲演会,请顾先生主持时,他便宣扬他的穆天子,说得 奇趣横生,天花乱坠,也颇有引人入胜之处。后来他的书出了版,果然是一本甚富学术价值 的著作,至于周穆王带领着三万数千大军自陕西出发,居然通过那么广阔的中亚,至于今日 的俄境,又曾居然抵达欧洲。道路的窎远,交通的困难,姑置不论,只问几万军队走在几万 里荒凉不毛的道路上,给养问题怎样解决?这个穆传讲疏却无交代。我以为研究学问是搜求 真理,搜求真理必须站在纯粹的客观的立场上,不容许有丝毫情感参羼其间。顾先生拥护中 国文化情感的热烈是有名的,这种情感若发之于抒情诗歌,或史诗,必能响出宏大的声音, 吐出熊熊的光焰,震撼一代的心灵,用之于冷静的学术研究,那结果便不一样了。十八年, 我夫妇又到苏州东吴大学,教过一年,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杨亮工校长写信来聘我。那时安大 颇延揽了一批知名之士如陆侃如、冯沅君、朱湘、饶孟侃、刘英士等。教务长兼文学院长程 憬,字仰之,北京大学出身,也许曾在清华国学研究所肄过业。他兼有几点钟功课,其中有 三小时是文化史。我到校时,有一门课我不愿教,钟点凑不出,仰之说自己行政工作太忙, 将文化史推了给我。我原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与“史”之一字从无交涉,这个担子怎挑得 起?仰之却说他可以将他编好的大纲给我看,再介绍几本西洋文化史供我参考,总可勉强对 付下去。我无可奈何,只有答应。 仰之那个文化史大纲共分八篇即A史前文化B太古文化C人类成人时代的文化D古文化 衰老时代E*幕?脑偕?贝F近世文化G十九世纪的文化H文化混合的倾向。每篇各酉改浚 ??形艺漳空也牧*编纂讲义。说他自己的讲义涂乙狼藉,字迹难于辨认,不肯出示,我也 不好意思强索。我在法邦学美术时,原买了几种美术史,史前艺术亦粗知梗概。我又有几本 法文本的历史书,前几章所论皆属史前文化,两河流域、埃及、腓尼基、希伯来、希腊、罗 马,虽属粗枝大叶的叙述,也算应有尽有。于是我的胆子骤然壮了起来,竟敢以一“门外 汉”教起程仰之让给我的功课了。 安大初建,基础未稳,学潮澎湃不绝。学生上课的时间,不及规定的三分之一。一学年 间,我的文化史只讲完了程仰之所示大纲第一第三两篇,即“史前文化”、“人类成人时代 的文化。”那第二篇太古文化,我认为可并入史前文化,不必另立篇目。我对鸿荒时代的人 类生活本来颇感兴趣,对两河、埃及、希腊、印度的古代文化也较爱好,以往关于此类记 载,比别的书是多阅一点,现在利用程先生所指示的参考书籍,及自己自法国带来的几本 书,将所得材料,排成系统,拿到教室去敷衍。仰之教此课时不发讲义,只口讲了,叫学生 笔记。我也照办。想不到学生对我这门课倒听得醰醰有味。有一个姓柯的男生上课尤其用 心,常借了我的讲稿去与笔记勘对。图画则照样描写了去。对日抗战时,武汉大学迁校于四 川乐山县,廿九年间,我住在一所小板屋里,一夕,夜已深,忽有客携灯来访,原来即是柯 君。他卒业安大后,赴美留学,学的是哪一科,今已不忆,只记得他曾说在安大听我的文化 史,印象颇深刻,赴美后,也曾选修了几小时这一类的课程。回国后供职重庆某机关,有事 过乐山,明早即将离去,在某一宴会上知我在此,辗转探问住址,因此来晚了。我那座板屋 位置于一大院落的最后进,上下石级甚多,白昼尚不便走,何况黑夜?柯君提着一盏昏暗的 菜油灯,磕撞久之,才找到了我的住所,其诚意实为可感。我在安大教的这门文化史,本来 是客串性质,不意因讲两河、希腊的文化,亦涉及神话,后竟成我屈赋研究的基础,可谓意 外的收获。 因安大学风太坏,一时难上轨道,国立武汉大学却有信来约我去。武大是国立,校规严 肃,誉满东南,时珞珈新校舍即将建成,出色湖光,映带生色,在那个世外桃源生活几时, 也是值得,我当然舍安大而就武大了。时为民国二十年。学校叫我承担的功课,是中国文学 史每周三小时,一年级基本国文每周五小时。文学史我从来没有教过,现在不但教,还须编 讲义发给学生。发讲义比口授笔记难得多。只好常跑图书馆,搜寻参考材料,一章一章撰写 下去。开始一年,讲义只编到六朝,第二年,编到唐宋。一直教到第六年止,我才将已编成 的讲义,加以浓缩,每章限六七千字左右,自商代至五四,一共二十章,成为一部中国文学 史略。 到武大的第二年,学校以学生要求讲现代文艺,即所谓新文艺,与我相商,每周加授新 文学研究二时。文学院长对我说,沈从文曾在武大教这门课,编了十几章讲义,每章介绍一 个作家。那讲义编得很好,学生甚为欢迎。他说着取出沈氏讲义给我看,我觉得并不精彩, 比他的创作差远了。像沈氏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吮五四法乳长大的新文人,教这门课尚不能得 心应手,又何况我这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半吊子”?况且,我虽未教过新文学,却知道教 这门课有几层困难。第一、民国廿一年距离五四运动不过十二三年,一切有关新文学的史料 很贫乏,而且也不成系统。第二、所有作家都在世,说不上什么“盖棺定论”。又每人作品 正在层出不穷,你想替他们立个“著作表”都难措手。第三、那时候虽有中国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左翼联盟、语丝派、新月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及各种派别的作家。可是时代变动 得厉害,作家的思想未有定型,写作趋向也常有改变,捕捉他们的正确面影,正如想摄取飚 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易。为了这几层难处,我向院长极力推辞,他强之不允,没法,只 有接受了。 接受了新文学研究这门课,果然就“苦”字临头了。我编新文学讲义与沈从文以作家为 主者不同,我是以作品性质来分别的,共分为“新诗”“散文”“小说”“戏剧”“文评” 五个部门,作家专长某一类文学,即隶属于某部门之下。那时候作家的作品虽不算丰富,每 人少则二三本,多则十几本,每本都要通篇阅读。当时文评书评并不多,每个作家的特色, 都要你自己去揣摸,时代与作品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又要你自己从每个角度去窥探, 还要常看杂志,报纸副刊,藉知文学潮流的趋向,和作家的动态。我的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 研究的讲义的编纂是同时进行的。我在后者所费光阴与劳力要在前者一倍以上。这新文学讲 义也是断断续续地编写,写了几年,才勉强将五个部门写完。抗战发生,武大迁川,只好将 这门课停了,于我原教的中国文学史外,又加了一班基本国文。 前文已说过,我每教一门新功课,总有收获。教新文学也有吗?收获也是有一点。我自 己那时也曾发表过几本作品,得厕于新作家之林,若从圈子内看新文学的面目定不能清晰,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今站在圈子以外,“成见”、“主观”均退到 一边,对于作家作品的评判,虽未能全凭客观的标准,倒也不失其大致的公平。我的讲义给 应赞美的人以赞美,应咒诅的人以咒诅,说丝毫不夹杂私人的情感是未必,说绝对没有偏见 也未必,不过我总把自己所想到看到的忠实地反映出来。有人或者说我臧否人物所采用的乃 是简单的“二分法”即凡左倾作家便说他坏,相反方面的便说他好,那也不然。当时文坛名 士十九思想赤化,我讨论叶绍钧、田汉、郑振铎、甚至左翼巨头茅盾仍多恕词,对于他们的 文章仍给与应得的评价。对于中立派的沈从文,文字方面批评仍甚严酷,即可觇我态度之为 如何。 我的屈赋研究是否也由于教书而来呢?答案也可说一个“是”字。民国十七八年间,我 撰写了一篇《九歌与河神祭典关系》(后改题为《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发表于现代评 论,以后对楚辞再没有讨论的机会。民国廿八九年,我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教中国文学史, 讲到楚辞部分,我写了一篇《天问整理的初步》那不过是一篇笔记,对天问的成因,虽推翻 王逸的“呵壁说”,代以屈复的“错简说”并说天问是可以整理复原的。我便试着来做这工 作。那篇笔记有几段导论可算我后来研究天问理论的雏型,将七言句归并于文末,作为乱 辞,也是那时开始的。因为对天问的内容究竟了解不够,故段落虽夺截分,文句虽有移置, 成绩却和屈复等差不多,说不上“复原”二字。到了民国三一年,卫聚贤先生说文月刊发行 庆祝吴稚晖八旬大寿专号,要我凑一篇,我原想将那篇天问笔记加以扩充,送去应景,谁知 竟发现了屈赋与世界古文化有关联的大秘密,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屈赋研究。这事我已屡述, 现不赘。我的九歌问题的解决也得力于教书。九歌为整套神曲,九神是同一集团的神道这个 原则之成立,乃由大司命那一篇获得正确解释而来。而这篇又由我在师范大学基本国文班上 讲解姚鼐泰山游记所引起。此事亦已屡次说明,现亦请从略。我过去教书从未教过楚辞,民 国四一年,自巴黎返国,授课师范大学,向学校自动要求教一门楚辞课。到成功大学及新加 坡南洋大学亦然。盖我深深了解“教学相长”这句话的重要性。我过去因教书得到许多学术 上的重要启示,教楚辞或者也不会落空。那时我的楚辞研究虽已得到正确路线,而那个宝库 入门的钥匙却未到手,无法打开,教这门课岂不是冒险吗?但正因我有冒险的勇气,竟能在 数年内将屈赋最重要的九歌天问陆续解决,虽说是意外的收获,也可说是意内。我们研究学 问的乐趣是发现。当我们发现古人或自然界的秘密时,乐趣之大即侯王之贵,百万之富,也 不愿用来交易。教书之际,能将你所发现的真理向学生宣布,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你说的话 太惊世骇俗,并且从来也没听人谈起过,总不免怀疑。几节课听受下来,听出头绪了,迟钝 的眼光发亮了,微笑不信任的面容变严肃了,从此便专心一志听受下去。你看了那种光景, 自己也感觉莫名的兴奋,恨不得将所有的心得,倾筐倒箧传授给他们,这时候教书的热忱, 真和充满神火的传教师一样了。民国五三年,我在台南成功大学教书在八年以上,轮到休 假,去新加坡南洋大学去换换环境。为了我能教的功课已有人教,一位师大旧同事让了我每 周三小时的诗经,另一位让出二小时的孟子。第二年又加楚辞三小时。诗经、孟子对我又是 新课,只好大借参考书准备。诗经与楚辞同属我国的最宝贵的古典文学,我既在楚辞里发现 了那么辽阔的新天地,对诗经也未免抱有若干的幻想与奢望。一年半教下来,才知诗经里除 了寥寥可数的几首与楚辞尚可相通外,其余便没有可以发挥的了。不过由于毛传、郑笺及孔 疏的启示,我知道了所谓“诗教”之由来,后代儒者著了一屋子的书来宏扬这个“诗教”是 什么缘故。这话说来太长,现在只有暂行搁起。 四书我幼时也算读过。四书中惟孟子文理较为显豁,故大部分可以读得懂。于今既教这 门课,不得不字疏句栉对学生讲解。孟子全文仅三万余字,每周二小时,一学年本可授完, 但以南大改制大闹学潮,耽搁功课约两月,尚有三分之一未讲。可是也在这门课上获得对这 位“亚圣”的新观感,将来若有机会拟写一本《孟子评判》。 教书顶好接受新功课,虽然比较辛苦,但它能拓宽你的视域,增进你的知识,加深你的 思境,并使你在学术上得到许多意想不到,极有价值的发现。若十余年老教着一门旧课,除 了开开留声机器,不能再做什么,那是没有意思的!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二期 5、三十年写作生活的回忆 若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倘使不算文白韵散,把 历史追溯得早一点,则第一部日记,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 因为自己的记性最坏,便是别人记得比较明晰的儿时事迹,我也模糊不清。若问我这部 日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实不能作确实的答复。大约不是十一岁半,便是十二岁,季节则 比较记得清楚,大约是气候清和的四五月之交。七八岁时,在家塾从一不通老秀才读了约两 年的书,夹生带熟,认得千余字。自己便来看小说,由说唐说岳看到西游封神,又看到几部 文言的笔记小说和聊斋志异,已懂得相当的文理,后来又看了六七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的林 译小说。小小心灵,陶醉于那哀感顽艳的文艺趣味里,居然发生了一股子阻遏不住的创作冲 动;又居然大胆地想尝试写作起来。记得那时在祖父钱塘县署中,我和大姊共一寝室,两张 床背靠背设在房子正中,天然把房子隔成两下,我的床在后,房中比较幽静的部分归我占 领。靠北墙有一小桌,墙上有一横形小窗,窗外有两株梧桐树,南风吹来的新绿,把满室都 映得碧澄澄的。我私自订了一本竹纸的簿子,每天用之乎也者的文言,写一两段日记,所记 无非是家庭琐碎生活和一些幼稚可笑的感想。大部分则是几只心爱小猫的起居注。文笔倒流 丽清新,隽永有味,模仿蒲留仙和林琴南的调调儿,颇能逼肖。写了几个月,居然积成厚厚 的一册,后因嗔人偷看,自己一把撕掉,烧了,以后也就没有再写。 自民国十六年起,我又开始作日记,直到于今,并未间断。这却是实用性质,半毫文艺 意味也没有,盖天公给了我一个相当过得去的悟性,却吝啬我的记性,事情过两三天,脑子 里所铭刻的印象便开始漫漶,十天半月,更忘得踪影都无,不得不以此为补救之策。每日所 记不过是几句刻板文章,脱句错字,到处可指,我常唤日记为我私人的档案,生前以备偶然 检查之用,最后则拟一概付之丙丁,是以并不愿用心来写,想到幼时的那一部,虽然思想浅 薄,却尽有些可诵的文章。况且其中又蕴藏着我无数快乐无忧的岁月,透露着我天真烂漫的 童心,充溢着我荒唐浪漫,奇趣横生的幻想。流光迅速,这部日记毁灭多年,我的最娇嫩的 青春也早已消失无余了,但有时偶然想起它来,我这干枯已久的心灵,常会开出一二朵温馨 的花;我的灵魂,仿佛被当年北窗下桐叶扇来的和风,轻轻送到那个罩在粉霞色朦胧薄雾下 的天地里去。 我的第一部日记可算是小品散文,第一篇小说则系十七岁的那年,以故乡一个童养媳故 事为题材的短篇。文章体裁仍然是我深受影响的林译体。前一年,我已写过一篇三四百字长 的五言古诗,题为《姑恶行》,现则又取其事衍为小说。 自己原是个整天笑嘻嘻,憨不知愁的女孩子,不知为什么,偏偏不工欢愉之词,而善作 愁苦之语。抓住了这个悲剧性的题目,用那古色古香的文言写出,却也写得辛酸刻骨,悲风 满纸,念给家里人听,赚了那些婆婆奶奶无数眼泪鼻涕。幸而没有漏到那做婆的母老虎耳朵 里去,否则我定要挨她一场毒打。民国八年秋,升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有印行年刊之 举,我将此文略加改削投去,蒙录取刊出。同班好友冯沅君欢喜骈四偶六,妃白俪青的六朝 美文,见我学韩柳体,常不以为然。我遂戏自命为“桐城谬种”,而唤她为“选学遗孽”。 沅君读了我这篇小说,又表示不大佩服,寄了一本年刊给她正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芝生,顺 便提及她对我作品的意见。不意她令兄复信,对我竟大加赞美,说我富有文学天才,将来定 有成为作家的希望。这位写中国哲学史那种精湛著作;抗战时期,又曾写过贞元三书的冯芝 生先生,原系我平生所崇敬的学者之一。每忆起他对我的案语,辄不禁窃窃自喜,自认果然 算一作家。但若干年以来,我虽写了一堆烂文章,出版过十几种单行本,纯粹文艺作品实着 墨无多,在文坛始终居于打杂地位。而冯芝生呢,屡次自己痛打嘴巴,宣言过去见解一概错 误,要根据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至于贞元三书则已早成覆瓿之 物,无须提起。可见这个先生的眼力本不高明,他那时一定将我估量错了,我也应该把他那 份好评语,原封不动,璧还他才是。 升学北京后,才和文言脱离关系,练习用白话写作。不久赴法留学,停笔数年。民国十 六年才又开始写作,发表两三本书,便在文坛取得了一个小小地位。 我虽不敢再以作家自命,三十年来这支笔却也从未放下,讲到写作经验多少总有一点, 不过我该预先声明,那都是我个人的罢了。一个人的写作生活也和我们普通生活一般,有生 来自幼至老,一帆风顺的;也有终身棘地荆天,过不着一天好日子的。在文章上说来,便是 文思的迟速,工作的难易,此乃与生俱来,非人力所能勉强。中外文学史对此两方面故事颇 多,不必絮叙。人家见我写作颇勤,误认为我文思相当快,其实不然,假如一天不作别事, 单坐着写文章,也不过二三千字。五六千则在精力最充沛,兴致最盛旺的时候才有,一生也 遇不见几次,古人所谓文不加点,下笔千言,伏盾可书,倚马可待,近代作家沈从文、徐*' 等为文不必起稿,所以敢把自己写得很清楚的原稿,印作书的封面;郑××经常日写万言, 怪不得他那么多产。我对于这类作家每羡慕不置,只恨自己学他们不来。写作生活中所遭遇 的困难,好像人生境遇暂时的顺逆,和那注定了永不改变的命运不同。我最怕的是日久不写 文字,脑筋像多年不洗擦上油的钟表,长满了锈,忽然碰着非担承不可的文徭,也只有强打 精神来写。那脑子里的机轴既开不动,拼命上紧发条,更着力摇撼,它还是如如不动,或滴 答滴答走两步又停住了。这时候做文章简直是一桩莫大的苦趣,本来想把一句话说圆,它偏 长出四个棱角;本来是一个极易表现的意思,却像沉在百尺井底东西,千方百计钓它不上。 甚至想觅一个适当的字眼,也要费上许多苦吟诗人推敲的工夫,运用一个易见的词汇,非翻 字典,查辞书,难得放心。一篇两三千余字的文章竟要两三日的功夫才能写出,而且文理还 欠条畅,气机亦不蓬勃。幸而第一道难关打破后,脑里的锈擦去不少,机轴可以开动,第二 道便容易得多了。少年时攻难关仅须几小时,中年半日一天,现在则需几天。最苦者,停笔 若干时,脑锈又生,继续奋斗,身体受不了,常钩起旧病。 个人作文的第二障碍是失眠。一夜没睡熟,第二天头昏脑胀,浑身不得劲儿,日常事都 懒得去做,何况这种绞脑汁的工作?偏偏我的神经素来衰弱,因衰弱而过敏,失眠也就成了 良朋密友,时来与我周旋。至若身上有什么病痛,譬如体内某器官发炎了,或某肢体作痛作 痒了,都会影响文思,勉强写了,也都是些应该打发去字纸篓的东西。 上述两个障碍,其一可以克服,其一也幸非日日有,但我还有个最大的仇敌,见了他除 递降书,别无他法。这个仇敌便是教书。西洋作家曾说艺术是个最妒忌的太太,非专心伺候 不能得她的欢心。我以为这个譬喻很确当,并承认自己情形确是如此。我是一个以教书为职 业的人,自小学教到大学。在大学我所担任的功课,少则七八小时,多则十二三小时。初教 的两三年,预备材料,编纂讲义,有相当忙碌,以后,则仅须开开留声机器便可应付。无奈 我那位欢喜吃醋的艺术太太和这寥寥几点钟的功课也不肯相容,定要实行伊邢避面。任你低 声下气,百般恳祷,她只是不肯出来。我教书已历二十余年,或者有人要问我,过去那一大 堆烂文章,和十几种单行本,不是这二十余年里的收获么?是的,但你们应该知道这都是利 用假期写的,假如把这教书的二十多年完全让给写作,我想至少会写出两三倍作品来呢。这 次来台湾,朋友知我有此病,劝我专以卖文为生,不必再做教书匠。但一个作家能以写作维 持生活,在中国恐尚属史无前例之事;何况我并非什么大文豪;更何况夕阳虽好,已近黄 昏,写作精力只有一年差似一年,何敢冒此危险?我个人的文思,不但是个善妒的太太,而 且还是位极骄贵的公主。她有时故意同你闹起别扭来,简直教你吃不消。关于这,我曾在另 一篇文字里详叙过,现且带过,以免重复。一个人的夫人若是个国色天香人物,则受其折 磨,亦在所甘心,但我的文艺太太,姿首其实平常,架子偏这么大,脾气又这么难于应付, “燕婉之求,得此夜叉”,真所谓命也命也,尚复有何话可说,咳! 每个作家写文章,都有其特殊的习惯,习惯有好有坏,我则坏的方面多。写作该有个适 当的环境,和得心应手的工具,所谓“窗明几净,笔精墨良”可说是最低限度的条件。我因 有眼神经衰弱症,光线过强过弱,都不能适应。像台湾这种迟明早晏的地方,上午八至九的 一点钟,下午六时以后我都看不见写作。况且我自幼至今,晚餐一下肚,便不敢提笔,否则 定然通宵失眠,这样子;写作时间当然很有限了。我理想的书斋是一间朝南的大屋,前面镶 着大玻璃窗,挂着浅绿色或白色的窗帏,早起见了那喜洋洋的日光映在帏上,满室通明,我 的精神自然振作起来,文思也比较来得流畅。焦黄粗糙的纸张和软软的羊毫或强头倔脑的狼 毫,每会擦痛我的神经末梢,勒回我的文思。甚至替学生改作文,见了太粗糙的练习簿子和 太潦草的字迹,也会起惹一腔烦恼,想撩开一边,永远不替他改。 我是不受拘束,随便惯了的人,写文章习惯不爱用格子纸。格子小而行列密还可将就, 格大而行疏,我的思想有如单驼旅客行于茫茫无际的沙漠之中,迷失了正确的路线。所以我 写文一向用白纸,行款相当拥挤,天地头又不肯多留,想改窜文字,每苦没有地位。在巴黎 二年,替人写稿博生活费,法国航空邮资贵而信纸则厚者多。一封航空信只容十六开信笺一 张半(香港带去的信纸则可容二张),我用蝇头小楷誊缮,每纸可写千余字。现虽已返祖 国,这积久养成的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希望将来能将字迹放大,再采用格纸,不然,常惹 编辑先生皱眉,校对员和手民咒骂,是很不好意思的。 或者又有人要问,你的文章产生既这么艰难,又不等着稿费买米下锅,为什么还要写? 写得还相当勤?这又应该归咎于我那天生的弱点了。自从在文坛上出了虚名以后,常有报章 杂志的编辑先生来征求稿件。我脸皮子最薄,搁不住人家一求,非应付了去于心不安。除了 讲演之约,我尚可咬定牙关,死不答应以外——因为平生最怕的便是这件事——文稿差不多 是“有求必应”。我的朋友袁兰紫平生写作惜墨如金,不但对编辑先生再三写来的信置之不 理,即使他们上门拜访,在客厅里坐上几个钟头,也轻易得不到她一个“肯”字。她常苦功 我早早将打杂生涯收起,写几部精心结构,可以传世的书。第一莫再做“滥好人”讨好编辑 先生,而误了自己。她这话未尝不是,但各人天性不同,我就学不到她那副铁面冰心的榜 样,又将奈何!再者,文章之为物,确也有几分神秘,它虽然从你脑中产出,却并不像那庋 在架上,藏在橱里的东西,你想应用时,一捞便到手的;它却像那潜伏地底的煤炭,要你流 汗滴血,一铲子一铲子挖掘,才肯出来。没有开掘前,煤层蕴量有多少,质地如何,你都不 能预先知道,甚至第一铲挖出的是煤,第二铲是什么,你还是糊涂的哩!也许是泥沙、狗 屎,也许是灿烂的黄金,或晶莹照眼的金刚钻,全靠你的运气!你若永远袖着手,也就永远 没有东西可得了。一个人除少时创作欲非常强烈,需要自然发泄外;中年忙于室家之累,没 有写作的心情;老年写文,有如老牛耕田,苦不堪言,谁爱干这样的傻事,不是人家催逼, 我们还有文章写吗?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打杂生涯,究无意义,我在这生涯上所滥费的光阴实已太多了,以 后想集中精力,做点子心爱的学术研究。“杀君马者道旁儿”,希望各报各刊的编辑先生, 体念此言,从此不再利用我的弱点来包围我,我便感谢不尽了?写文章像用钱,有支出无收 入,高积如山的财产,也有用完的日子。我们想写作内容充实,应该读两种书,第一种是有 字的,各图书馆和大书店到处都有。做个文学家并非能运用几个风花雪月的字眼,或喊几声 妹妹哥哥便可以了事的,顶要紧的是有丰富的常识,所以读书不可不博。不但与文学有关系 的书该读,便是没有关系的书也该读。不过对于书中材料,做蚂蚁工作不够,还该做蜜蜂工 作。否则食而不化,纵然胸罗万卷,也不过是个两脚书橱而已。第二种是无字的,要你自己 在人情上体会,世故上观察,企图成功为写实作家者,此事尤不可忽略。女性作家宜于写新 清隽永的散文,或幽窈空灵的小诗,大部头结构复杂,描写深刻的社会小说,则少见能者。 所以密息尔的《飘》,凯丝铃·温莎的《永恒的琥珀》,无论批评家有何歧异的意见,本人 则甚为钦佩,认为难能可贵。我本来无意为小说家,更缺乏禹鼎铸奸,温峤燃犀的手段,能 将社会各阶层牛鬼蛇神的面目,一一刻画出来。为善用其短计,要写小说,只有写历史和神 话小说。过去对此也曾略有尝试,惜写作嗜好太杂,没有弄出多大成绩,将来倘机会许可, 我还打算再来一下呢。 如前文所叙,倘将影响我写作的爱读书范围也推广一点,不论文白韵散,则说话便容易 多了。幼时爱读聊斋志异和林琴南早日所译的十几部小说,这是我的国文老师,它瀹通了我 的文理,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它的恩惠,值得我感念终身。又有一部商务出版文言译的天 方夜谭,文笔雅隽遒炼,实在林译之上,我也得过它的好处。所谓四大奇书也者那四部章回 小说,中国知识分子谁没读过?不敢相欺,我因读书快又有喜读已读书的习惯,自幼至今, 每部至少读过六七遍或十余遍了。幼时爱西游、三国,长大爱红楼、水浒,于今则连我国人 最崇拜的红楼,也颇不满意,认为算不得全德小说。不过我的白话文的根底,乃此四书培养 而成,不能否认。我现在欢喜读的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乃是蒲留仙的醒世姻缘传,此书当然 也有其缺点,譬如那些迂腐可笑的因果报应,那些堆垛重累的描写,那些夸张过度的点染, 也着实有些讨嫌;但其刻画个性,入木三分,模拟口吻,如聆謦?;尤其在那个时代,作者 敢于采取自己家乡的土白来作书中大小人物的谈吐,使得他们的影子,永远活动在我们眼帘 前,他们说话的声气,永远响在我们耳鼓里,所以这小说实是百分之百的活文学,也是中国 第一部写实的社会小说。时代尽管变迁,它的价值是永远不朽的了。我虽不善写实,又未常 试为长篇,对于此书读虽爱读,受影响实谈不上,但过去几篇历史小说实由第一次读此书后 创作欲大受刺激而连续产生的,《蝉蜕》那一篇影响更较为明显。旧式短篇白话小说,我觉 得今古奇观究竟不错,可说“老幼咸宜,雅俗共赏,盖幼时读它是一层境界,长大后读又是 一种境界。俗人读仅知故事有趣,雅人读则知其中有许多篇文学价值颇高,值得欣赏。 诗歌方面,自少时所读唐诗三百首及少许选读汉魏古诗不计外,十五六岁时,父亲买了 二部木版小仓山房诗集给我。这部诗集有点注解,虽不大详细,但少年人脑力灵敏,善于吸 收,看完后胸中平空添了许多典故,并知道活用的方法;以后又得到一部杜诗镜铨,所知典 故更多;以后,又自己抄读了不少李太白、李长吉、白香山、韩昌黎、苏东坡、陆放翁、高 青邱、王渔洋、邵青门等人的作品,不惟从此会做各体诗歌;词汇,辞藻,亦收罗了无数, 让我在各种写作上应用不匮。现虽十忘七八,但写作时尚没有捉襟露肘的地步,不得不感谢 我自己以前所用那番工夫。 外国作品,我爱荷马的伊里亚德、奥德赛那两部史诗。全部希腊神话——包括后人改作 改编的在内。及巴比伦、埃及、印度、犹太、波斯及其他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故事。欧洲十 九世纪象征主义和唯美的作品我均爱读,并深受其影响。自然主义的作品,我始终爱那位短 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左拉虽为自然主义的巨子,他的作品我实不会欣赏。觉得巴黎万神庙 收葬左拉遗骸,道路亦有以左拉名者,而独不及莫泊桑,实有欠公道。大概因他那支笔太尖 利,剜人疮疤太厉害,惹了多数人的憎恨之故吧。 总之,上述喜读之书,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约、或自己清楚觉 得,或完全出于无意,对于我的写作生活均有帮助。老实说,一个作家,也决不是上述寥寥 几种书便影响得他了的。他该一面写,一面收集资料,细大不捐,兼收并蓄,取精多,用物 宏,写时自有左右逢源之乐。若叫他呆板地举出几部喜读而又深受影响的书来,他只有大睁 两眼,对你望望罢了。顶多也不过像我今天应编辑先生之命,胡诌几句交卷,有什么意思 呢! 原载《读书》半月刊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