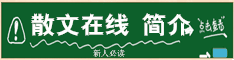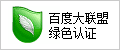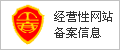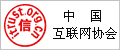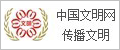散文在线:原创散文发表网!致力于打造中国最专业的原创散文网!
消失

时间:2011-11-02 10:02
散文来源:本站原创
散文作者: 寒流涌进点击:次
|
今天,我以拐为腿为脚蹒跚学步似的向前走着,我携带着已残疾的身躯在今天的道路上摇来晃去,到处都是今天的时空天地。这样走着,不再回程,一路走来,一路消失。消失在展现中消失,展现在消失中展现。昨天脚下踩过的砖石不见了,昨天走过的小路不见了,昨天见过的房屋不见了,一眨眼工夫曾见过的都不见了。今天有多少消失未留下痕迹,记忆的空白处,印象的缺失处,生命源头的地带,到底有过怎样的展现与消失?一个幼小的生命与一个拄着双拐的残疾人,其中到底有过怎样的断裂和连接?今天我两手握着腋下的两只拐杖,无论怎么努力,从生命的这一段也够不着那一段的边沿。
那一段的边沿是一个朦胧的黄昏,一条食堂大门外的小路,小路上走着一个瘦高的男人和一个幼小的生命。男人的肩头是一条扁担挑着两只沙锅,锅里盛着一家五口人充饥的稀汤菜饭。这样步步走向靠近家的地方,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一只沙锅不合时宜的与路边的一块青石交锋,这样的交锋,自然是不堪一击的沙锅破裂,充饥的汤饭未走向等待的肠胃,趁机一跃而出,不管不顾的钻入碎石的缝中。
记忆到此断档,那断档的后面是何种的意境和意象,已是一片混沌的迷茫,而锅底碰击石头的声音,是怎样转瞬即逝的轻微?可这种可忽略不计的声音所造成的事件,似乎蕴含着巨大能量并穿越岁月的时空,今天仍在时不时的叩击着我的心壁。它产生的后果,让一家五口人的肚腹从空洞的期待走向期待的空洞。
今天,沙锅的破裂、稀汤菜饭在碎石小路上由点及面的滚动,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的沉默,那个属于我自己的幼小的生命,一家五口人在黄昏的煤油灯下单调而沉闷的叹息,这些都如一根根银针刺穿我生命的记忆。
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所有的眼睛都封锁着梦境的甜蜜,所有的梦境都推上甜蜜的高地。上工了‑‑!上工了‑‑!一个声音从一个叫做队长的汉子口中跳出,打破村庄的宁静。喊声,一声紧接一声,钻入一家家房门、穿越村庄的上空。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告别暖暖的被窝、揉着惺忪的睡眼、迈起脚步,不紧不慢,似乎看不见速度。顷刻,脚步踏过地面,如鼓点密集,踩响一个村庄真正的黎明。
村口,一个面向的目标,多少年不变的定向,多少年不变的脚步。脚步聚拢,人影攒动,宛如一个汇聚的码头,从这里集体起航。村口,显示队长高度的地方,队长将劳动的任务下达,瞬间,一群叫做社员的男女身携锨攫锄耙、箩头扁担走向养育生命的土地。
我那时听从过队长的指派,去完成一些皮皮毛毛的任务。春天舀粪点种,夏天锄地摘择果蔬,秋天我常拿着一把小镰或一把小钁。我那时还没长到一个标准的大人,不算一个合格的社员,因而仅能干一些无需技巧的皮毛小事。没想到当时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会成为我这生作为一个农民体现的一点真实意义,因为这类小事在我即将成人的那一年就截然而止。从此,它们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队长,一个曾经响亮而权威的词;社员,一个曾经光荣而自豪的词。它们像一对恋人,相伴而行,又中途分离。
夜晚,油灯昏暗,灯光摇曳,一个称作记工员的人趴在桌边,一手握笔、一手按纸,依序填充着用圆珠笔复印成“姓名、摘要”的白纸表格。
夜晚,一个个走向土地的身子调转进印证着自身价值的门坎,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自己的名字,盯着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数字,宛如盯着在土地中奔走的一个个日子。
有人盯着,目光开始扭曲。即刻,嘴与嘴交锋,肯定与否定对峙,唾沫星翻飞,变换的脸色最终敗給不变的夜色。这样的夜晚全因了一个斤斤计较的数字。
我从不过问工分数字。记多记少,记与不记,不与计较。那时,我对农活不懂技巧,只知吭哧卖力,于是那记工的表中,从未有过我一工满十分的数字。那时我人小体弱,劳动全为一种乐趣。
一个夜晚,因争辩变得热闹而生动。一个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计较工分,就是计较生命,自己的生命,一家人的生命。
饥饿,一种感觉。当饥饿与万物复苏的春季相遇时,往往陷入青黄不接。
当第一声春雷在辽阔的长空炸响时,一年之际在于春的土地与咕咕乱叫的肠胃同步陷入急不可待。当饥饿像个淘气的孩子,不依不饶成为人的拖累时,最终,母爱的土地做出了退让妥协。
那时,我常坐在春回大地温和的风中,看着一个个提着空空的布袋奔来走去的身影。他们从我的身边走过,低着头,好像去办一件不可见人的事情。当这种躲躲闪闪的形态被一张坦然的笑脸替代后,借粮这件难以回避的事,已经磊磊落落地占据了普遍的中心。我看着一个个补丁摞着补丁摞成厚实的布口袋,在我的眼前空去空来,或是空去满归时,我空瘪的肚腹就会感到更加难耐的空洞。
这样的日子,走进期待耕耘和播种的土地,会看见很多小草已生根发芽,破土而出,抢先占据土地的位置。
饥饿,一个曾经有血有肉很饱满的词;饥饿,一个离我们今天向前奔走的脚步越来越远的词。
借粮两个字,如一对孪生兄弟,曾经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在山村山野中奔走。今天,它们背离着背、山隔着山,路途遥远,谁也不再见谁。
一面山坡下,一条小河旁,垒一圈乱石,抹一圈稀泥,留一个火口,坐一口大锅,山野沟壑中,一种叫做集体的大锅饭的形式即以构成。
炊烟缭绕,烟尘飞舞。灶膛口的人不时的吞吸着浓浓烟尘,烟尘制造的效果是,起伏不定的哮喘、捉摸不透倾吐的浓痰、眼睛里不时滚动着不是心酸的泪水。
山地上劳作的社员,不时将身子调换成眺望炊烟的姿态。眺望炊烟就像眺望连心连肺的亲人。可炊烟只是在由淡变浓、由浓变淡的变换,从不管那一张张期待的嘴。肠胃咕咕叫着与手下的农活对抗着不愿妥协时,很多目光就不断的伸向救助的天空,可天空依然是无边的辽阔,太阳仍在不紧不慢的运行。
开饭喽——!开饭喽——!盼望的声音总算想起,宛如等来的一个期盼已久的喜讯。手与手相拍、掌与掌相击、嘴与嘴高叫,都表现着心中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激动,都为了填充一个空空的肠胃。飞跑从山地中开始,跑向山道、跑下山坡、跑向那个大家共享的地方。谁先跑到大锅的身边,谁就抢先靠近叫做饭的物资。顷刻,一支锅碗瓢盆的交响乐就拉开了序幕。
我那时对大锅饭也是心有所向,心中常常像盼着喜庆节日似的对它盼望,盼着它给予一次稀缺的丰盈,盼它填充一次空空肚肠,盼它给焦躁的心魂一次平和的安适。大锅饭,一天又一天,我们相依相伴,一起走过一段难以忘却的时光,
大锅饭,一年又一年,我腋下多了一副拐杖的那一年,拐杖支撑着我走进故乡的土地时,它仍然以锅、以饭展示其大,依然是原来诱人的模样。
我常看见父亲在村中曲来拐去的窄径小路上匆匆奔走,奔走时手里常拿着一块长条形木质印戳,印戳的一面刻着一个凹形而工整的五角星。
父亲除了它的名字外,还有两个供大家称谓的字:保管。在农村,保管与粮食紧密相关。生产队的粮食存在集体的楼上,粮食用编织的苇席由低而高一圈圈围拢而成。父亲每次取过粮食后,都会小心翼翼的把打乱的粮食重新扒拉平整,接着父亲就会在平整的表面轻重有度的按下一个个清晰可辨的印记。每次印过后,父亲都是紧锁眉头,默不作声,表情严肃的一遍遍数点着五角星的个数。
那时我年幼不懂事,不懂那印戳的重要,不懂印戳肩负的使命,不懂不应打乱一个平面的完整。我常常借着一个可将自己垫高的木凳,将父亲已装在心中的五角星破坏得不见踪影。冷不丁,我柔嫩的小手挨了一巴掌。父亲其实下手很轻,我却以疼痛的理由裂开小嘴嚎啕大哭,发泄心中的不满和委屈。
今天,父亲已离我而去,但我却难以忘却他一次次将屯集的粮食打乱、一次次小心翼翼将粮食的表面扒拉平整、一次次毕恭毕敬的按下棱角分明的五角星印记的身影。今天,我已多少年未听见过自己委屈的哭声,但留在岁月深处我生命之初那种不懂世事、不懂痛苦、不叫委屈的嚎啕痛哭稚幼的哭声,让我感应到遥远的亲切,让我知道与生俱来的一种液体叫做“眼泪!”
五角星,以特殊的形式刻进我的记忆!
场院,一个村的中心。这里凝聚着春天的孕育、夏天的成长、秋天的成熟;这里可看见汗水浇灌的色彩、躬身培育的果实。
一个汉子、一头牛、一个石磙、外加一顶草帽、一条鞭子和一把为牛处理粪便的锨,他们组成一个合作的整体,在场院为秋天敞开的胸怀,一圈又一圈,碾压在秋天的一道程序,逼近着秋天的本质。
一把干净的木揿,在场院的风中很优美的扬起,很优美的落下,借着风向将多余脱落、内外分离。一个与土地有缘的农人,练习多少年,才掌握了这种技巧,才算一个真正的农民。
一杆秤,在场院高高举起,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一张张嘴久久不肯闭合。这样的情景展现在收获的秋天、秋天的场院。场院,一堆堆金黄的玉米,一堆堆鲜艳的果蔬,在汇聚中等待,等待那个最终分配和认领自己的主人。
场院,一个理论得失的场所,秤高秤低,缺斤短两,都会引发一场互不相让的争吵。在这个喧嚣嘈动的地方,我常常默默的从称钩上接过一篮豆角或一篮玉米,一转身,我久久凝视着秋天的青翠和金黄,会生发很多捉摸不透的思想。
场院,一个与村人命运息息相关、一个凝聚与扩散、一个充满着生机又消磨着生机的地方。今天那个属于生产队的场院已不存在,但它追随着我的记忆,一步步走进今天的时光。
有一种液体,它以隐蔽的流动,连接和展示鲜活的生命。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液体的时候,知道了我们体内有这种物质在无时无刻的流动,知道流动就是流动生命。那是在一条连接着两个小村的坡道上,坡道上滚动着很多碎小的石头。我默默的看着一滴滴汇聚的液体在坡道上的碎石中如蚂蚁爬动时,突然听见身后一个凌空炸响的声音:血!从此我记住了这个与生命有关的字,记住了我们体内一种流动的物资,记住了一种鲜红的颜色。
我知道,我看见的这种与生命有关的物资,是从一个很绵
善的本家爷爷的体内流出的。他被一边一个汉子扭胳膊摁头护送着向另一个自然村的会场箭步如飞的狂奔。护送,是我能想到的两个字,后来知道了一个准确的词:押解!上坡时,爷爷冷不防一个趔趄,面朝下狠狠的摔了一跤。随即,他就像个弹簧似的从地上弹起。这种瞬间转换的过程,归功于那两个汉子的四只手,那四只手像抓小鸡似的把爷爷从地上抓起。这之前,我时常看见爷爷慢慢腾腾稳稳实实的在村中走路,从未见过他放开两腿奔跑的样子。
后来,爷爷回归原来走路的样子时,我看见爷爷的嘴唇皮光肉厚的肿胀,裂开的嘴中,前门已空缺无物,两个门牙不辞而别,留下一个不挡风的空洞。
山村的夜是黑暗、寂静、孤独、零散、漫长的综合体。用什么高亢的声音可穿透夜的脊梁?用什么不安的动荡可震撼夜的胸膛?一条没有动感的木质板凳走进夜里,站在夜里,让我很多年都难以忘记这样的板凳。
一个什么分子站在一条木凳上,他弯着腰、低着头,这种样子叫:认罪!从弯腰到抬头,又一个词叫:示众!一群人围着,都喊着一种声音,于是凳上的分子就频频的低头认罪、频频的抬头示众。这样的夜让人只知嘴快速的张合,忘记很多喜怒哀乐的事情。这样的夜最后定然推向高潮,高潮的结局是,那条站在夜里的木凳和木凳上的躯体一头栽向坚硬的青石铺砌的地面。这样的结局肯定是一只脚、两只脚、几只脚伸向木凳,一起用力,木凳一个摇晃,在夜的腹部重重的划开一道口,成为夜的创伤。
随着木凳倒地,我赶紧拔腿跑离会场。我一脸惊慌跑出很远,想着鲜红的血怎样破皮而出、怎样在地上流动、怎样在地上由红变黑的凝结、风干、消失。
我的少年时代和任何一个孩子一样,曾坐在课堂听老师讲课,曾因一些题的疑难紧锁眉头。后来的经历就不堪回首,可我又再度回首。
讲台上站着我们的老师,顶天立地的样子,我们坐在讲台下认真听着老师为我们讲课,从无知到有知,从混沌到开悟,从空虚到充实,都归功于老师渊博的知识和思想。
后来,老师还是老师,书本却不知为何收藏;学生还是学生,却失去学生的模样。讲台上,那张不动的书桌却悄然离去,老师无依无靠的站着,已不是出口成章的讲课。学生反小为大,一次次振背、一次次高叫,愚昧的学生给智慧的老师出的题,老师却口齿木讷的回答不出。老师不断的弯腰、不断的低头,像个听话的孩子,我却不知不听话又会怎样。
一面金光闪闪的铜锣,被老师正儿八经敲击得山响。老师在前,学生在后,从学校走进村庄,走进一条条七拐八弯的青石铺展的村道上。学生们的手,落下举起、举起落下;学生们的嘴频频开合,开合中,像夏日的惊雷从头顶轰然滚过。
我站在人群中,听着老师握粉笔的手敲打出的“咣咣”的声音从耳边飞过,从山村高低错落的房屋中飞过,从山村的上空飞过,飞向村外辽阔的山野。在这铜锣的声音飞起飞落中,我一次次听见这种铜质的声音在远山的悬崖上处处碰壁,碰壁的同时,又一次次将那原质的声音迎击回我的耳朵。
学校加个七年制,是我这生的最高学业。那里是我人生的黄金岁月,但今天才知道已成为我不可补植的沙漠。今天,不知我尊敬的老师们都去向何方,但他们在我的梦中活灵活现,我仍然是长不大的学生,他们仍是永远不老的老师。
煤油灯,以弱小抵抗强大,以一点之光打破夜的统治。
父亲手握一支长长的旱烟袋,将自己坐成油灯下虚虚实实的影子。父亲将粗硬的手指合拢,从一个黑色的小布袋里捏起细碎的烟末,慢悠悠的装进烟袋嘴里,继而是点燃、吞云吐雾、磕掉、再装上的过程。这样重复的过程,让沉寂失去支点,让时间失去漫长。
奶奶借着晃动不安的灯光,从衣襟下掏出带着体温的肚兜,将昏花的目光聚焦在一道细小的裂口上。紧紧盯着,抖动着手缝合。拆了缝,缝了拆,一阵吃力的穿针引线,一个小口终于在曲折的手中将一段时光闭合。一个裂口消失,几张零碎小钱重新进入自己安稳的窝。每每看见奶奶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缝纳肚兜、数点贴己小钱时,我就猜想,那贴身的肚兜一定是奶奶一份心存的依靠和希望。
母亲借着油灯昏黄的灯光,数点着叫做粮票和布票的纸张。母亲常常盯着盯着眼珠就一动不动,那模样会让我想着粮食、粗布、肠胃和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我背负过很多补丁的衣裳,我知道那都是母亲温暖的思想。一个补丁盖一个口,很多补丁盖一个口,数着补丁,就像数着母亲灯下的身影,就可懂得补丁下浓缩的漫长。
一块白布,母亲可染成各种颜色。年节,母亲坐在油灯下,飞针走线,给一家人赶做一次没有补丁的衣裳。年节,我穿着母亲用染料遮蔽着白色、一年一度没有补丁的新衣裳,笑着、乐着,甜甜美美荡满心胸。
油灯,我人生光明的向导,我亲情甜蜜的储藏。
有三个农村的孩子一直未离开我,在我的心中走着、跑着、跳着、笑着。还有三头牛拉的车,一直在我心中吱呀有声的滚动着。
三个活泼的孩子,三辆滚动的牛车,三头肥壮的犍牛,一条条通向土地的山间小道,组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时光。
从村口的牛圈到一块块排列在山坡上的梯田,是一条条坑洼不平的坡道。我们三个体力不够的孩子,在牛圈互帮互助的装粪,路上相互照应着护车,走进土地,我们三张小嘴齐声喊着“一、二、三”,将满载的粪筐揿翻在土地宽厚的胸怀。此时我们的气喘声与牛的呼吸声一样,汗珠也滚动上额头,可我们却轻松的笑着,因为我们觉得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为生产队运送着牛粪,也为自己运送着时光,今天很多经历业已忘却,可这件运粪的小事却像种下的种子一样在心田茁壮成长。今天,那三头伴我们三个孩子曾一起奔走、奔跑的犍牛也已从存在回归虚无,可那铁论滚过地面、牛蹄踩踏地面的声音,老牛粗壮的呼吸声,我们三个孩子奔走奔跑和说笑的声音,如一首不老的歌,穿越岁月的长河,让我依然听见它的歌声。
一种让饱满的颗粒碎裂的声音,一直撞击着我梦中的耳膜,我知道那是村头那盘老碾任劳任怨的思想。
青石为盘,青石为磙,一根穿磙而过的长条圆木,共同构成一盘老碾真实的形状。乱石围砌三面壁墙,椽檩搭拱一面顶棚,构成老碾不受风霜雪雨侵袭的居所。
个儿瘦小得够不着碾杆时,我和小伙伴们在碾道中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后来我成长到可推动石碾,我开始在碾道中不停的奔走,奔走在生活的圈定,奔走着为家人卸一份沉重。
石碾,一村人走来走去,在走来走去中连接起一种淳朴真挚的浓浓情愫。石碾,以破碎养育生命,以足迹印证时光,以无私和包容不遗余力的奉献。
离别多年又回到故乡,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老碾。我与双拐相依相扶着一步步走向老碾,想不到村庄里已没有了它的踪影。在老碾原来的地方是一座拔地而起崭新的楼房,从楼里走出的面孔透着一种距离的陌生。我知道,老碾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老在岁月的途中;我知道,我也一步步走在老去的路上。今天我寻它不见,它见我不能,都注定是一段存在和不再存在的时光。老碾何人建造?何时诞生?它伴随而养育了几代交替过往的村人?这已是一个谜,我永远无力揭开。
我在故乡的村庄寻找着我曾用过的一把锨、一把钁、一把锄头、一条扁担等与土地有关的农具。我在想着曾有多少伴我成长的农具让我无情的丢弃在岁月深处。今天,我和拐杖寻找在光洁鲜亮的村庄,但寻找的结果是它们都早已不知去向。
我可以拿着任何一把农具走进土地时,我会感到我的每一次心跳都来自大地母亲的心脏。今天我因为腋下的一副拐杖,背离土地已很久很远,不再走进,难以走进,愧对土地,愧作农人。这是我一生难以消除的疼痛。痛在继续,不再继续的是那时的生活形态,那时的自然生态,那时自然起落的风雨,还有那时存在过的所有生灵,今天都已消失净光。
今天,村庄处处都是焕然一新的景象,一张张面孔透着年轻的陌生。村庄,已不见了祖母父母和我所有熟悉的老去的面孔。母亲走时,两眼紧紧盯着我,盯着盯着“咕咚”一声就走了;祖母走时,体内的元气已耗尽,一丝声音没留下就悄没声息的走了;父亲走时紧紧握着我的手,嘴一张一合,很想给世界留下几句最后的声音,那声音里定然有对我这个伤残儿子生存的担忧,但最终他还是没能吐出一个字,遗憾的走向另一个世界。生命离去时有很多方式,但我知道并不轻松。
消失,是新旧交替、时光流动,但我不知眼前流失的那一刻,又有多少新的消失和新的诞生。
赞
(散文编辑:月然) |

------分隔线----------------------------
- 优美散文
-

-
- 莫言苔儿小,恰是君子身
“ 净与溪色连,幽宜松雨滴。谁知古石上,不染世人迹"。"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
- 偶遇
岁月漫漫,彼此遇到过,温暖过,而后铭记于心,同样也是一种美好的结局。...
- 你的福气皆于善良
当生命旋转到一定的年轮,对尘世的细微之处,就越发不舍得忽略。这是岁月的醒示,让人...
- 诗意的人生
日子总是不乏诗意的,可我们有时觉得,日子并不那样的清澈,让人徘徊在一片茫然之中。...
- 心存信念 一苇以航——读《堂吉诃德》有感
在浮华与坚守之间,现代人将如何选择?喧嚣嘈杂的浮华社会,有些人们的灵魂早已蒙上灰...
- 吾心安处是故乡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
- 本版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