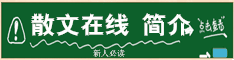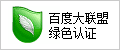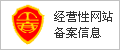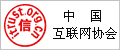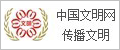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男性的尴尬
———兼及《红楼梦的》“性别观”
一
《红楼梦》只一部书。百人读之,有百说;千人读之,有千说。
但对曹雪芹而言,他只有一个“我”,一个性,一个情;发为万语千言,不外一份
心思。这“心思”曾是鲜活的。当悼红轩主人永逝林泉,后人大抵只能在《红楼梦》
时处处,不都是曹雪芹的笑貌音容?
突然生发的潜意识未经论证,就窃窃私语了:《红楼梦》是一部男性化的书!
别”。由作者之“性别”,推定作品之“性别”,这是简单易行、却难脱其谬的招式。因为,中国文学史上并不缺乏男人写“女儿书”、或女人写“丈夫词”的成例。李易安“人杰”、“鬼雄”之愿与温飞卿“画屏”、“鹧鸪”之恋,确曾在颠倒衣裳后呈现出奇异之美。稍加推求,这或者便是文学精神的一雌雄异化或文学角色的男女反串。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并未刻意于艺术精神的“男扮女装”;只因为《红楼梦》展示了“大观园”的女儿世界,弥漾着挥之不散的红粉艳香,故而世之读者竟对曹雪芹的须眉气度投以怀疑。这倒应了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禅关机语。曹雪芹纵有百口,亦说不清自己在他的作品里是须眉精神,还是裙钗风范。
二
“我”乃“堂堂须眉”,“我愧有余”,“我悔无益”,“我之负罪”,“我之不肖”,“我”
之“将真事隐去”,“我”之“用假语村言”,等等,无一不是作者想一次性地明告读者
结撰这部大书的人文立场和艺术焦点。“立场”(或视角)是充分男性化的,“焦点”则是男性对象化的女性。简言之,《红楼梦》写男人,是男人的自愧、自悔、自责或自励;《红楼梦》写女人,则是男人对女人的理解、同情、爱恋、或歌颂。角色不论男女,皆着上男性的色彩。
《红楼梦》的评点派人物太平闲人说:“石头是人,是心,是性。”这很正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人”是男人,这“心”是男人的心,这“性”是男人的性。一个男人,用他的眼去看,用他的心去思,用他的笔去写,一部表现他“孤愤”、性情的小说问世了。精神产品属于精神创造者,《红楼梦》的“男性精神”最初也是属于曹雪芹的。
在《红楼梦》的流传史上,评点派、索隐派们都注意到了作者“剖心呕血”、“胎里带来”而著书,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学传承、从社会历史与人生、从男性女性的两相依存上去剖判红楼作者的“男性觉醒”。孤立考作品与孤立考作者,终究缺乏人性透视的深度。
质疑自有其理。但是不可忽略上文所谓“性觉醒”的命题。“男性精神”,是“男性觉醒”后的生命精神。男性,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女性”命运纳入同一个生活范畴,因而也将自己的生活权利与女性的生活权利连带思考、等量齐观时,他才算获得了“醒”。《红楼梦》里,贾宝玉是“男性觉醒”的典型。埂峰下的那块顽石,因为娲皇的煅炼而有灵性,他又用得之女性的灵性浇那绛珠仙草,仙草遂“得换人形”,“修成女体”。石遗人间为男主人公,草降人间为女主人公,一部《红楼梦》才演义了男欢女爱的宝黛恋情。女性孕育了男性,男性灌溉了女性,男性女性结合为生生不息的生命之链。《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天上背景,是作为贾宝玉的宿命渊源和男人的灵性寻根而展开的。这是大有意味的一笔,可惜读者、评者都没有从男女二性的“原始依存”上透视其文化精神的隐喻。
与《红楼梦》的“男性觉醒”相比,《三国》、《水浒》乃至《西游记》都欠缺着历经淘洗的“男性精神”。《三国》是男儿戏,女人仅仅是男人做戏的道具。《水浒》也是男儿戏,女人往往在“男性化”后失去涵育男人的魅力。《西游记》亦是男儿戏,女人在“妖邪化”后甚至成为男人“修行”向善的恶性诱惑。上几部小说虽然写男写女,但是都没有从生活、生命的相互依存上揭示“男性觉醒”。《红楼梦》可资借鉴的人文精神,只有到《金瓶梅》里寻觅。当曹雪芹扬弃了兰陵笑笑生的“女性偏见”时,《红楼梦》才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张扬了较为清明的“男性精神”。
三
粗浅地论析到这一步,我以为已经接近了本文对《红楼梦》作“性别鉴定”的主体意识。所谓“男性”的书,所谓书的“男性精神”,哪儿是“唯男独尊”的“大男子主义”呢!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麻木的男性膨胀“消肿”之后,“三国式”、“水浒式”的男子汉大丈夫彻底幻灭,代之以不文不武的“小男人”粉墨登场。
告别了前代小说“大男人小女人”或“好男人坏女人”的模式化处置,《红楼梦》决意在“家”的社会结体里安顿它的男男女女,或许是艺术上的矫枉过正,或许是与以往小说人物的对比过于强烈,《红楼梦》塑造男性形象时给予了更加严厉的男性自审。当然,这“自审”大都囿于精神的、或“意淫”的层面。
“意淫”者,情也;情者,男女之爱也。能“意淫”与不堪“意淫”,又将红楼梦男人分为高下二类。高者,以贾宝玉为典型;下者,姑且以薛蟠为典型。不论情欲与肉欲,在它们追求发泄的过程中都充分地揭示了“小男人”的灵肉之斗。这种自我的搏斗,常将“小男人”们推入尴尬之境。
尴尬之一:是他们不能有好女人。贾瑞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秦钟差可比之。“性”成熟,“情”还稚嫩,于是有贾瑞的叔嫂之衅及风月之鉴。贾瑞的追求在“镜”中,这是一个彻底虚幻、却异常燎人的陷阱。死而不悟,非贾瑞一人也;淫邪之病,亦非贾瑞一人也。十二回贾瑞死,十六回秦钟死,用这两例死证,预为警戒天下须眉,作者的忧怀不独萧墙之内也。
尴尬之二:是他们不配有好女人。贾琏可以为一代表,贾赦、贾珍之属皆应归入此列。有一副臭皮囊,吃一份官禄粮,承一番父祖业,少一挂好肚肠;如此,一种自大自肿的情怀醉得他们不能与好女人平等相处。过滤了“情”,残留下“色”;放纵了“色”,酝酿了“乱”;贾琏的“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最后导致鸟飞兔走。
尴尬之三:是他们不敢有好女人,我选柳湘莲为代表。这位世家子弟,读书不成,耍枪舞剑,赌博喝酒,眠花卧柳,原非忠厚之辈;但尤三姐却一见引为知己。三姐与湘莲相比,定然是“好女人”。但柳湘莲的假撇清却让他自陷于虚假的“石狮子论”不能自拔;该爱而不敢爱,尤三姐伏剑自明其志。柳湘莲的情感失落,偏见使然;待他自叹“没福消受”时,然不明白是“没胆相爱”。
尴尬之四:是他们在拥有最充分的机缘时却丧失了爱的兴趣,此谓不宜有好女人也。贾宝玉为其代表。宝玉之“性”初醒,在第五回;“性”尝试,在第六回;其时他年仅12岁。“性”的苏醒引带了“情”的发动,一部红楼,芟刈枝蔓,轴心故事是贾宝玉的“情史”。虽然警幻仙子给贾宝玉“定性”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但那理论依据是“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极端之词;考之贾宝玉的日后作为,倒是在“性”初醒“性”尝试后,以过来人的灵智,厌“性”而恋“情”,表现了难得的洁白。或许有了这段“性”、“情”转折,或情感“质变”,他与林黛玉的爱情才是纯洁的、美的、高尚的,却又是虚幻的、脆弱的、病态的。在家族合力的摧折下,当宝黛的“超性之爱”被粉碎,贾宝玉的精神之恋再也不能还原为肉欲之恋,所以他的“昏瞆”之病,“出家”之行均在生命的必然之中。
四
女人是“神”。女人的第一个群体在“太虚幻境”,自成一个警戒性的、可以启发男性走向精神成熟的超验系统。作者安排贾宝玉在警幻仙子“导游”下游“太虚幻境”,进“孽海情天”,阅“薄命司”《金陵十二钗正册》及“副册”、“又副册”,听新制《红楼梦》曲,品“千红一窟”茶,饮“万艳同杯”酒,直至体验“儿女之事”,皆大有深意存焉。除小说结构性的需要外,“太虚幻境”女神世界的创造主要是先入为主地肯定女性的“精神价值”。这“神”的世界,“女神”的群落,与小说下文大观园“人”的世界、“女儿”的群落,形成暗寓性的观照;因此,一切“神”的、“女神”的肯定都是为了投射为“人”的、“女人”的肯定。
女人是“水”。这“水”,是“五行”之“水”。在与“土”的对立中,《红楼梦》将女儿的“水”的特质强调到极“美”的层面。“水论”的发明者是贾宝玉。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现代心理学当然已明确测定“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生命倾向,但是贾宝玉对女性“水”性反响却超出了表象化的直观性,“清爽”的感受源于“质”的洞悉。薛蟠之混浊,贾环之俗劣,贾赦之庸碌,贾芸之浅薄,固“土”性太重也。即如进士出身的贾雨村,“浊”在“贪酷”;袭官为宦的贾敬,“浊”在“好道”;“平静中和”的贾赦,“浊”于“太好色”;“端方正直”的贾政,“浊”于“迂疏肤阔”……贾府内外,一应男子,无不浊声而浊气。即便最有思想、个性的贾宝玉,比之林黛玉、比之薛宝钗,其诗文机智和处世谋略仍有捉襟见肘的差距。贾琏知书达理,能力在目不识丁的王熙凤之下,贾蓉风流倜傥,心机之巧远远落于秦可卿之后。夫妻比较的阴盛阳衰,又非上举一、二例也。“水”失之“柔”,“土”失之“浊”,似乎各有所短;但从灵智方面看,“水”的清澈流丽,终于胜过“土”的木讷不仁。荣宁二府之所以弄到“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问题便出在“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儿孙”的“退化”,有如沃土渐趋瘠薄;以“土”喻男子,确乎哉!
在《红楼梦》中,作者还通过他的“男性视角”发现了女人在“家庭”或“家族”中的关键作用,即:女人是荣、损之“根”。《红楼梦》中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原是从政治联系的角度概述官僚家族运的。对此,小说倒没有太多的印证性描述。
我们看的,却是因为女性的存在或女性的荣辱,连带了“家”的及家中“男人”的升沉。贾府的兴衰,依持两个女姓,一是史老太君,即贾母;一是贾元春,即贾皇妃。因为贾母的存在,荣、宁二府才实现了“五世同堂”的大团圆。因为元春贵为皇妃,荣、宁二府的贾家才沐浴皇恩,中兴了渐趋没落的家道。尤其是元春的入宫,直接导致贾府的“升格”。“江南织造”,再富有再显赫,也是皇家的奴才;而一旦有女为妃,贾家自然成为“贵戚”府第。如果认真地掂量一下贾元春的政治分量,可以说,无贾元春即无今日之贾府,无大观园,无大观园内的众姐妹,即无《红楼梦》故事。
五
如果说女性的“价值”,有时还可能被男人漠视;那么女性的“美”却大都是被男人首先发现、且乐于称道的。折射到文学上,表现女性之美的几乎垂延为不断线的传统。只是就小说、就长篇小说而言,女性“美”的展示还多停留在“声色之美”的层次;女性“才思之美”直到《红楼梦》面世才被充分挖掘出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男性偏见地肯定女性的形体美和心灵美,自《红楼梦》始。我赞成涂瀛的说法。曹雪芹心如“度花之风”,笔如“照花之月”,才使《红楼梦》“主持巾帼,护法裙钗”成“大块之文章”。“一念之仁而众美各若其性,一念之义而众美各畅其情,一念之礼而众美各忘其形,一念之智信而众美各尽其才,各尊其位而已也”。这儿,涂瀛阐明的还是作家与作品人物的相通,以及作品人物形神之一统。
关于《红楼梦》女性美的命题,极为深邃而广远。本文仅有“略述”之旨,而无详叙之幅,故只能指出数景,仰天叹星也。略而再略之后,我想引述的是这么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大观园这一少女世界的美学暗示到底有何人文价值;一是红楼闺秀的悲剧是否触及了美与毁灭的必然联系。
《红楼梦》的少女世界,是中国艺术的奇观。如果说《水浒传》让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梁山泊还有历史上的绿林英雄为参照,《金瓶梅》让一妻五妾团团围定西门庆还有明中叶的世态时尚为佐证,《红楼梦》将数十名黄花少女召唤入大观园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一种“幻造”,亦如他幻造了“太虚幻境”。从艺术上讲,这叫“创造”,这叫“集中”,这叫“典型化”。“事实”的合理性,也是超常的———“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贾元春晋封“凤藻宫尚书”、“贤德妃”,故有“省亲别院”之“大观园”拔地而起,又有“穷亲”投奔,黛玉、宝钗、湘云、香菱等人之聚,水到渠成也。
“女儿国”建立了。这是一个精神联系的群体。精神的相互辉映,使这一群体更其亮丽。这是一个拒绝男性介入的世界,阶段性的拒绝,使纯净的女性美免受污染。“在山泉水清”也罢,含苞花最美也罢,少女的美仑美奂都具备“精神酝酿”的价值。保住这少女“山水”的圣洁,实际上就保住了男性(丈夫与儿子)精神源头的清纯。换一句较为时髦的话说,大观园充满女儿之美时,无异于中国道德精神的“基因库”里藏有至宝。
“美与毁灭”,撞响我们心中悬挂的那只悲剧之钟;《红楼梦》里,残存着粗心人读不懂的钟鼓之谱。作为小说,《红楼梦》之前之后,确实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如此忍心地将少女的死亡逐一展示于读者。以“死”衡“美”,此“美”重于泰山而又轻于鸿毛,这则因人因缘而异。“死”,并不是刻意毁灭“美”;有时,倒是“美”去追求这生命的无牵无挂。阅读《红楼梦》,我们时不时又被“美的尊严”感动。因为“毁灭”,因为“死亡”,“美”意外表现了它的完整性。林黛玉如此,晴雯如此,尤三姐如此,鸳鸯亦如此。所以,在“形而上”的理性青空,“美”永远是飘扬不逝的呼唤。
回落到生命的埃土之上,我当然知道用社会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男女对立的眼光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研讨“美与毁灭”的关系。这是言之不尽的话题。倘若在这无尽的话题之后,仍然等不来男人们对男权社会的反思,甚至引不起一缕男性尴尬,那么,《红楼梦》是白读了;与曹雪芹那个“男人”相比,我们这群“男人”无疑是精神残缺的。
女儿们不妨看红楼,但那是另一回事。
(刊《东方文化》1999年第4期)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