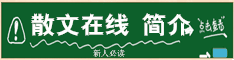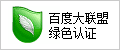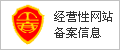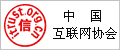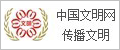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怕啥呢?” “坟山上才埋了死人——吊死鬼!” 平常哪家死了人,发丧的日子,我是不敢去看的,怕做恶梦,让我夜里怀了许多的联想,想那人还是生前活着的样子在路上走着。坟山上新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因为失身而吊死了。吊死鬼就埋在坟山上的桐子树下,没有花圈,只是一根竹竿上挂了几条白幡,白光纸就在风中飘曳,发出哗哗的响声。女子生前是大队宣传队的演员,一个漂亮的女靑年,除了她红脸唱戏的样子,又是别队的,我并不认得她本来的面容,却常听到社上人们对她的议论,不知怎叫“失身”,只觉是掉下悬崖了。因为不是光彩的死去,亲人也没有让她体面,只是草草的埋了。坟小而萎琐,连望山门也没有,这一走,连冤魂也是进不了家门的。打入另册逐出了家门去的孤魂野鬼,更别指望亲人来烧纸化钱了。这种女鬼最具煞气,特别是青年的男子很容易中邪,在“五·七”三十五天前是万万不能靠近坟地的,她的灵魂正在找替身。 半下午的坟山光秃秃的没有人声狗叫,远山白平观的檐角似乎传来风铃的响动,荒荒的,森森然,吊死鬼坟上的白光纸在阳光下翻飞起舞。坟山上少有人来,草鲜嫩起来,山雀在桐子树上啁啾,新坟上的土晒得苍白。仗着胆子走到桐子树下,看见新坟前烧着一堆黑灰,是女子生前的遗物,一块没有烧尽的花布被昨夜的雨洗得分外鲜艳,仿佛女子生前的花容。一只黑蚂蚁沿白幡的竹竿往上爬,爬上顶端,举首投足,却找不到上天的路。 坟地的冷清,心生奇怪,牛却并不理会我的心境,低头专心吃草已穿过了坟地到了一处悬崖。我怕它“失身”,忙把它牵回来,有了牛,心里的恐惧消失了,生命于自然是崇高的。我把牛拴在黄荆上,爬上桐子树,可以望到远处劳动的人。一阵风来,先是看到从麦地那边绿浪一般涌过来,到了坟山就散了,消进了坟堆的空隙,只有高际的树叶摇动;风到了桐子树下被树冠挡了,在壁障形成一道旋风,卷起了坟前的黑灰,那块花布翻过来,飘过了树叶,如一只蝴蝶飞走了。 陡里子有人正从坟山的出口崇上来,一个捡粪的少年挑了牛屎筐。农村上,半节子娃儿在队上出工又不够劳力,只有靠捡粪来挣工分,常跟在牛屁股后面,放牛娃叫他们“刮屎匠”。捡粪的少年进了坟山好象并不介意桐子树下的新坟,在坟山转一圈,发现树上的我向我笑了一下,一直走到吊死鬼的坟前,放了挑子,捡起女子遗物中没有烧坏的一颗有机玻璃纽扣,然后吹了吹灰,放进自己的口袋。已是夏天了,我己穿著新买的白市布衬衣了,他还穿着初春补丁重补丁的千巴衣,洗得干净,针脚讲究,是缝纫机补的。我正孤单,招呼他上树来,周围方圆几里捡粪的我都认识,他我没见过,看他粪筺里的牛屎巴,也不是刚上路的生手。他猴子一样上了树,自我介绍叫杨树章,邛崃杨家湾的。也难怪保胜这地方五县交界,难免遇到外县人。 “咋你一个子呢?” 我指指新坟说:“都怕吊死鬼。” “人死如虎,虎死如肉。” “啥子意思呢?” “人死如老虎一样吓人,虎死了只当是肉。” 是道理。 他聪明,很醒世的样子,眉宇间一副精灵。想他已经读书,今天是星期二,队上的学生都去上学了的。 “你逃学狗?逃学狗不读书,先生逮倒扯耳朵。” “读过两年书,现在没读,读不成了。” 说着他拿出几本图书。《地雷战》、《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全是打仗的,我非常欢喜地看起来,他靠着我一起看书,有声有色地读着,让我不曾识字的心生敬佩。他问我读几年级了,我说明年才上学。 “读书好安逸啊,可惜我这辈子读不成书了。” “咋个呢。” “我爸爸死了。” 我看看他,心生叹惜,一个没有爸爸的人就读不成书,爸爸是读书的保障。 看完一本图书,天就暗了。奇怪的是,这天下午牛没有屙屎,而还有两本图书我也没有看完,依依不舍地还给杨树章。他说,两本图书你带回家看了改天还我,对我这么信任,要知道借书不还,迷藏起来是常有的事,何况是生人。我很过意不去。别人对我这么好,我却无以报答,见他粪筐空空的,叫他给我走。 到了我家后门的时候,我让他在树林里等我。把牛拴在树上,确信周围没有人,才让他跟我进牛圈。庆幸的是父母忙,没来得及掏牛圈,一堆新鲜的牛粪还留在角落里,给树章掏了在粪筐里,稍嫌不满,又从粪坑里捞了些往日打整的干粪把粪挑子装满。树章很高兴,又有点偷的意思在里面,紧张的看着我行动。装好了粪担,树章挑起要走,我又从柜子里抓了一把胡豆给他,他异常感动,不说话,挑起粪担三步并作二步,一口气挑到大坟山才敢歇气。 老天爷已开始卖麻布了,白天已从远山褪下来,送进了染坊,越染越黑,树章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己汗流浃背。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挑的担子,连大人都吃力,我让他倒些在黄荆笼里,明日再来挑,他不肯。天渐渐的黑了,离邛崃杨家湾,还有四五里路远,我担心他能否挑得回去,他很有把握地说没问题。目送着杨树章走过黄山埂的羊肠小道,半暗的身影象一只猿猴子学做人的样子,望着黄山埂上孤独的棬子树,失落又惆怅。走过大坟山,桐子树的阴影下,新坟上除了白光纸划过的弧线,没有一点颜色。如果今夜有雨,明天那一点白色的影子都不存在。后来呢,那坟成了放牛娃爬树的阶梯给踏平,连一点点留给人的恐怖都没有了。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把树章和那坟里的女子混为一团,这种奇怪一直到现在。 以后我盼望见树章,他却一直没有来过大坟山,二本图书我已看过好多遍,树章依然没有来。这些日子,我都去了大坟山,天天看见吊死鬼的新坟。队上的伙伴都赶牛到白平观山上去了,我天天到大坟山,格外的想念杨树章。我的孤独跟失去他的友谊有关还是中了女鬼的邪,天天来坟山约会。从初夏到盛夏除了几天下雨封了门的缺席,我都在后门看图书,想着那坟,和树章在桐子树上的样子,甚至我未曾谋面的吊死鬼的音容笑貌都清晰起来,以致上了初中,高中,我在图画课的时候,常勾勒她的形象。后来,那女子的兄弟和我成了同学,看了我的画像说是他姐姐。我才知道,那一年我一直中了她的邪,在苦难中让她的灵魂渡过无边的苦海,重回我的笔下再生。 直到有一天,我背着书包上学了,树章来到我家,那天我在后门背课文。 我似乎已经忘记了树章,树章和一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脚有点跛,力气已大了一点,挑粪担的样子比以前轻松,尽管他的劳力足以胜任全劳力,年龄让他还是未成年,不能成为公社的社员。 晚上我留树章在家住,他不肯,说是母亲要寻他,在我的执意强迫下,他才算留下来。父亲很喜欢我的朋友,一是树章的勤劳和朴实,二是树章没有父亲,他把父亲几乎当了他的父亲。后来我们造房的时候,他帮了很多的忙,还偷了根树来送我家,父亲说:偷梁换柱,家道可以改观。晚上我们上床摆了会龙门阵就睡了。半夜的时候,后门突然响起敲门声,我忙起床开门,后门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苗条,白净。我把她让进屋,点上煤油灯,看她很幽怨的样子,误把她当作了吊死鬼,愣在那里,这时树章也起来了,他叫了声:“妈,你咋来了。” “天黑了也不落屋,我担心。” 透过煤油灯的光,我觉得树章的妈好象我想象中那个吊死的女子。以后我学画时都把她作模特来画那个女鬼的倩影,竟然被女鬼的弟弟说就是他死去的姐姐,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想树章妈妈不是一个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不应该有这样的身段和美丽,整洁的头发一丝不乱,谦卑中有高贵,这样的母亲如何有这样可怜的儿子,我的联想总是衔接不上。 父母听到响声也起了床,看见树章妈,忙烧火做饭。树章妈说:“吃过了。杨树章给你们添麻烦了。” 大人把儿子的姓和名连在一起喊,这尊重中有苍凉的味道。 “没事的。”父亲忙说:“娃儿家耍得了情义,舍不得分开。” 话毕,执意的母亲已端了碗荷包蛋上桌,放到树章妈的面前,这是家里对最尊贵的客人的款待。 树章妈一再推让,道谢,就是不肯吃。最后,还是我和树章一人一个消灭了。 天不早了,我和父亲送树章母子俩回去。到了他家的外面,没有进屋,只是在井坎边,看他们走进了竹林。几声狗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喝叱声,似乎听到一阵重创后树章的惨叫,被他母亲哀求的哭声掩盖了。 我心好痛,想冲进去,被父亲拉着了。一路上,我想父亲会责骂我,是我的缘故给树章带来了痛苦。父亲没有说话,以大人的沧桑抚着我的头。这在我心里埋下了太多的困惑,对树章家的神秘让我一夜未眠。树章不是说他爸爸死了吗,那豪叫的男人是谁? 树章这些日子都没来,我已在龚石小学读二年级了。到了星期天,实在忍不着,便骑了黄牛径直的去了邛崃杨家湾。下了石厂坡,一片柏树林的下面就是树章家,那天晚上看不清楚,这会真切的见了是一幢很气派的瓦房,吊檐讲究的漆了油漆,垂巴墙也粉了白壁,阶沿的梯步,石砌得匀称。木骨窗是雕花的,一围木槿花围院。树章的妈在井边洗衣服,美丽韵致,脸上泛红,见了我恍然大悟,忙向菜园地里干活的树章喊:“杨树章,你朋友来了。” 声音柔弱,振作了精神才喊出来的,她站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红云褪去,现出一脸的的苍白。 树章见了我手脚无措,一双线耳子草鞋沾满了泥巴,他妈让他歇会,他这才陪我。我告诉树章,我的牛还拴在柏树林,他便和我去了柏树林。柏树林是老林,大战钢铁后幸存下来的,因为关系着杨家湾的地脉,更重要的是杨家出过一个大人物,柏树林就是他的宅基,才有理由保存下来。林子已没有房屋,只存一些残垣和断壁,杨大人的后人做官在北京,先前是有房子的,在京做官的杨家后人好象遭了,没人管也就破落了,一对石狮子威风凛凛的镇守在宅基。林中的几棵古柏已伸过了后山的岩头,几里远的地方都可以望见,周围的柏树是近年栽的,象列队的士兵护卫,阔展着柏树林主人的气派和风光。 树章把牛牵到一个有草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上山,山上几亩种过花生的地,已种了麦子,还有一行一行的空隙待种。树章扛了锄头在空地掏花生,掏了几行,收获甚微,他一个也舍不得吃,全给了我。他对我的到来诚惶诚恐,不知所从,东一头,西一头,心里边好象怕发生什么事。到了古柏下,他有意的在茅草上寻什么东西,果然捡到了花生。听到树上的鸦雀在叫,才明白是在鸦雀失口掉下来的。我数了一下,古柏有十二棵,上面的枝叶交织在一起,住着一群山鸦雀在枝上嬉戏,摇得柏树籽索索的落下来,有整块的枯朵铺了在石阶上,蚂蚁在上面搬动,阴凉里,透着柏油的香气。树章在树下搜索了一转回来,捡的花生,有的已被雀啄破了壳,或是只有半节豆,他全塞进了我的口袋里,我也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吃,俩人靠着石狮子坐下来。树章低着头,往日和我一起时的活泼不见了,满腹心事似的,见我注视他,他勉强笑了一下,说:“晓的山雀生蛋没有,我爬上去取雀窝。” 说完,他已攀着古柏相邻的一棵仔树,伸手搭过老柏的横枝,跨到了大树上,树上的鸟遭到侵袭,呱呱乱叫,盘旋在树的上空。树章直捣雀窝,向我叫喊:“五个雀蛋!”。 “我看一下。” 他拿了两个跟我看,白生生的嫩晃,我喊: “全取下来。” “要不得,我取三个,窝里留两个,留点余地,要不雀就不来了。” 他脱了上衣,把雀蛋放到口袋里,两只袖口挽紧,我站在树下准备接,他却把衣服牵开,象一只蝙蝠滑翔下来,轻轻的降到了草丛。我跑了过去,雀蛋完好无损,白里透红的圆润。 树章从树上下来,我本以为他会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他却没有这层意思,我找喝水的借口,他才带我去了他家,家里有他的两个双胞胎兄弟在做作业,一身穿得伸抖舒气。我和树章进去,他们视而不见,树章好象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更不屑他的朋友了。 树章到灶房舀了一碗凉水,我喝了水,把剩下的泼到院坝里,那做作业的俩小子睨了我一眼,他妈洗了衣服晾在菜院的木槿花篱栅上,亦静若寒蝉。 木槿花的院外,突然响起了自行车的铃声,做作业的小学生忙跑了出去迎接,进来的是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为人大块,把自行车架在檐口,没把我们当回事,只是问做饭没有,下午还要开会。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红光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树章的继父。 树章带我回了树林,又去玉米地里匀了玉米秧子喂给黄牛,黄牛懂人情世故似的屙了一堆牛屎,算作对树章的谢意,我深知树章的为难,便告辞走了。临别他拉着我的手,情深意切尽在其中。 回家后,每天清早打扫牛圈,把牛屎偷藏一些在后门的土窖里,等树章来挑。如果他三五天不来,又怕牛粪干了,就扑一些水润着,等他。再有三五天不来,在星期天我就骑了牛,用肥料薄膜口袋装了牛粪给他驮去。一个人去大坟山放牛,总是把牛屎藏在古墓,留给树章来捡。 到了二年级暑假,已和树章同等的学历,他对文字有很好的天赋,悟性也比我高,丢了书本好几年,读过的课文全背得。假期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些,不是他到雷塘碥耍到深夜,就是我去柏树林看书学画得很晚。到了晚上天暗了,余兴未尽,我们就采集了桐子果,用铁丝穿了燃烧作照明,看他父亲留下的一本《芥子园画谱》。山水,虫草,鸟都有详尽的笔法,先是手痒,在残壁上鬼画桃符,后来裂皮的古柏,闹枝的山雀成了我们写生的对象,还有黄牛的神态在树章的笔下也是千奇百怪。黄牛也亲近树章似的,屎尿很少在圈里屙,总是留在柏树林,母亲说牛爱干净了。 暑假里,树章向我说了他的身世,我们更成了亲密的兄弟。 树章的父亲是教书的老师,被打成右派,受不了斗争摧残悬梁自尽。家境从此便衰败下去,母亲又是地主小姐出生,虽有文化却是一个被遗弃的人。父亲的归天,让她一病不起,因为成份不好强赶到队上出工,内外交困得了痨病。母亲后来嫁给了死了老婆的大队革委会主任。从此树章的天空就苦风凄雨,母亲愁容郁结成宿命,劝树章忍气吞声,勉强留他下来。树章还有个妹妹,远在蒲江林雨,由舅舅带养着。况且主任也根本不认这门亲,舅舅和母亲也就断了往来,与其相见锐利的痛苦,还不如痛断那份思念,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已不能正常出工,只是照看一下家务,这无疑对母子的处境雪上加霜。他体谅母亲,放弃了读书,让继父的双胞胎儿子读书,这才有了一家的和谐。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又挑起粪担挣工分。母亲心里安慰,却常常担心小小年轻的树章伤了身子骨,可是她只要稍有袒护,便遭来咒骂:“活鬼,咱汤倒你了,还白养你儿子。” 树章几次想带母亲走,可是能走向哪里呢?母亲对树章最有效的保护是刻薄,而对主任的小子照顾周到,这样的厚此薄彼,平衡了家庭。无事安身,是树章母亲的人生哲学。只有私下里,她才心痛树章,常对儿子说:“穿孬点,才能吃好点,忍得气,才长得大,苦命人都是耐大的。你是杨家的根,还有个妹妹的将来要你照看,如果我不在了……”妈妈总是説着就伤心。十二岁的树章已是一个朝天的百姓了,他懂得天底下最不平的路是留给自己的。 我的生日到了。妈煮两个鸡蛋,这在我认识树章后,每年的生日都多了一个。我把鸡蛋留着等树章来。但树章收了礼,从没当我的面吃过。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升到三年级了。树章恳求我,三天教他一次,和我一起读完小学的书,我有些为难,不过我还是答应了。因为只一本课本,树章就偷那兄弟的书,因挨了打,便用白纸全部抄了课文,我们一星期一聚同步学习。 队上的伙伴很看重我的朋友都帮他捡粪。树章爱助人为乐,在雷塘碥都知道是我的朋友,一年里除了他家,多半都在雷塘碥过。 至今记得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刚收完谷子,我留树章在家吃了新米饭。社上的伙伴都来约他耍。他讲的故事现在想来是他牛吃笋子屙背篼,牛肚子头——编的。送树章回去的时候,他说好想他妹妹,己有六年没见了。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路去。去蒲江到林雨少说也有六、七十里路,一天怕是走不到,我说我们骑着牛去。 第二天一早,我告诉父亲去杨树章家了。 开始走山路,我们一路走一路让牛吃饱,到了回陇镇上了大路,俩人骑在牛背上就赶牛跑进来。到了蒲江县城已淡黑了,还有小半的路,我们加紧赶路,一路星光,到林雨已快鸡叫了。她妹见了我们骑牛回来,好生奇怪,见了生人不大说话。树章妹妹要比树章高一点,这是树章劳磨的故,才铁疙瘩不肯长。妹妹像母亲长得眉清目秀,读书矮我一届,堂屋里的墙上贴了她很多奖状。她对哥哥很亲,跟树章说话的时候,小大人似的带有点训人的口吻,树章总是点头,看着妹妹学习身体好,心里很高兴。舅舅不在家说是去修朝阳水库去了。 和妹妹耍了一上午,吃过午饭,我们就要走了,树章说我明天还要去上学,妹才同意让我们走。临走的时候,树章要了一张妹妹的照片,是学校颁发的“三好生”奖状照的,回去要让母亲同享妹妹的优秀。妹妹还一人送了我们一张手帕,是他学做的。我说妹妹到哥哥家的时候就去我家玩。 她送我们到朝阳水库的时候,见到了舅舅,舅舅是水库工地的通讯员。他嘱咐树章要好好善待母亲,送了一支笔和二本稿签子给树章,要他自学读书成材。告别了舅舅,妹妹又送了我们一程,说过了再见,还跟在我们的后面,树章生气了,她抱着树章哭起来。 “哥,我想妈。” 树章也哭了。 “明年暑假,我来接你去看妈,听话。” 妹妹放声地哭。 树章让我骑上牛,她跟着走,我们策鞭跑起,转过山弯,还看见妹妹爬上山头,望着我们远去。 开学了,我的一知半解不能把知识很好的传授给树章,树章很希望亲自听老师讲课。我们的教室后面的窗子很高,有一片桑树林,树章就爬到桑树上偷听。一次老师提问,他在树上忘了身份举手大声的回答,被老师发现,老师出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跑了。同学们告诉老师,树章是我的朋友,张老师听了,让我转告树章他可以在树上听课。树章听课按时做作业,张老师也认真给他改。 可是好景不长,树章的母亲在五月的一天,说是在井边提水的时候,一时虚脱栽进了井里,等人发现的时候,已无力回天。树章知道这一消息,跪在母亲的遗体前一直起不来,无语无泪,我告诉他去接妹妹来不?他只是点头。 连夜我骑着牛去了林雨,先在朝阳水库找到舅舅,才回家接妹妹,妹妹问我哥哥为啥没来呢,我只是说他脱不开身。舅舅在工地请了假,要明天才走得了,他骑自行车。我骑牛带妹妹先走了。妹妹骑牛害怕,紧抱着我,随牛的步伐自然起落,也就不会掉下去。背后是妹妹娇小的身躯,我生怕她得知失去妈妈的噩耗而支持不着。一路上我想着树章兄妹今后的日子,眼泪止不着的纷飞。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母双亲,这样起飞了,羽翼还没有丰满。如果我是一个济苍生的英雄,我会踩出一条大路让他们走,让他们走进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 妹妹见到母亲的时候,我的笔己无力再复制当时的个情景,几十年了,我依然听到她凄厉而撕裂肺腑的哭声,想到天上的扑食秃鹰扑向地上哭泣的婴儿。 从此,树章和他妹妹随舅舅离开了杨家湾,回到了林雨。 母亲的死拯救了树章。 他们的母亲就埋在石厂湾那块光秃秃的山上,相邻的是他父亲的坟,周围没有一棵树,只有石匠在岩上錾下的无字碑。天下雨的时候,山上的沙凼畜满了雨水,就会从岩上淌下来,打在石窟里,发出幽怨的空鸣。 四十年后,我在书店,看到一本子矜的小说《古柏》,知道就是当年的杨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