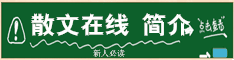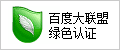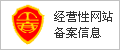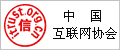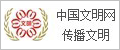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记忆中有许多词,我是从娭毑、太娭毑她们那一辈人嘴边捡拾的,比如“细媳妇”。
细媳妇
幼时没文化,无数次从娭毑那辈人闲聊中听她们说起“细媳妇”,听见了就听见了,并不当回事,照样偎在她们身边半眯着眼睛装老实。稍大,略微识字时,也不当回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细就是小的意思,顾名思义:细媳妇就是年纪小的媳妇,如此而已。
后来,我妈与娭毑之间爆发了一次较激烈的争吵,才觉得这“细媳妇”应该不是个好词。
性子较急、做事风风火火、脾气也跟她做事风格一样的我妈与老实木讷、胆小懦弱的娭毑是两个极端。虽然如此,也极少如同队上有些婆媳之间,今天婆婆骂得媳妇去跳河,明天媳妇气得婆婆去吊颈。当然,小磨擦肯定有,只是我娭毑很能容忍我妈妈的火爆脾气,不大理会她。
那天,不知怎的,两人本来好好的在灶屋里煮饭,突然传出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娭毑说话声轻轻地,听不大真切。我妈噪门很大,不需费劲就能掩盖住青菜在热锅上的炽烤声及灶堂里芦苇燃烧时的“哔啵”声。
“说我娘屋里没陪嫁?你看这屋里的蒸钵、木桶……哪一样不是我出嫁时带来的?不说别的,你老人家床上那床十来斤的大棉花盖被还不是我的?我进门时,你屋里有什么,除了欠一四散的账……”
“你就莫说你娘屋里有好富足,你看看今朝子谢家屋里收的那个媳妇啰,花花绿绿的,硬是派了七、八个后生子才挑回来。你那时有多少东西,我还不清楚,和被窝一起也没有两担……”‘穷人争饿气’,娭毑的声音也扬高了些。
谢家那媳妇的陪嫁,说到底我妈也是蛮羡慕的。羡慕归羡慕,她总不可能去怪我外公外婆,她在家中最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要养活,我外婆身体又不好,总不可能为了这虚面,把家底全搭给她。“我的陪嫁当然比不得她的,我那是七、八年前,但总比你老人家好一点,娘屋里养你不活,让你几早八早来熊家里做细媳妇,还跟我管陪嫁。你娘屋里这么多年,可给你置过一根纱……”
娭毑一听这话,火钳“啪”地一声掉地上也不自觉,愣愣地怔了好久,才知觉回归似的,冲出小小的灶屋,跑到茅草房后,抱着一棵并不十分粗壮的水杉树嚎声大哭……
“妈妈,什么是细媳妇?”我妈并不搭理我,只是默默地捡起火钳往灶堂里塞柴火,火光亮时,她脸上也一片晶莹。她哭什么?
到底什么是细媳妇?它在年少时我的心中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记不太清,只大约记得乡下如果见别人畏手畏脚、说话细声细气、胆小怕人,就会骂他“你类,像细媳妇一样……”,这样细媳妇应该是受尽委屈、好欺侮的人的代名词。再长大些,我找到了答案。“细媳妇”便是书上所说的童养媳,是旧社会时,女方养孩子不活,把还小的女儿送给比自家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人家,让他们帮忙养着,长大了就给他家其中一个儿子做媳妇;也有男方家庭条件不好,怕自家儿子长大后娶不到媳妇,就到别人家领养一个女孩,长大后,让其与儿子成亲。当然也有家庭条件好的也把女儿送给人家的,反正养女儿是帮人家养媳妇,不如早些送给人家;还有两家交换着养的……很显然,娭毑是属于前者,我妈不经大脑的一句反驳,“娘屋里养你不活,让你几早八早来熊家里做细媳妇……”应是勾起了她隐忍了几十年的疼痛。幼时被父母遗弃,来到一个不熟知的环境,“吃人家的嘴软,到别人家后,要手脚勤快一点,莫讨人嫌……”离家时,母亲含泪的嘱咐,在时光里不再是温暖的念想,而是一块强迫自己压抑本性的巨石,于是,她面对公公婆婆的苛责可以一忍再忍;壮年时夫死,也没想到过回娘家寻找一丝帮助,顶着婆婆近乎变态的指责,独自忍气吞声为四个崽女忙碌,及至儿女们都成家后,又像没有任何思想、思维的木头人般听儿女们的吩咐。也许也有“多年的细媳妇熬成婆”的希冀,可是试了几次后,发现世道变了,她还是不能堂而皇之,如同她婆婆那样在儿媳面前指手划脚,只能畏畏缩缩地做着她自认为最讲规矩的事,比如,家中来了客人,她都会小心翼翼地躲着客人;过年过节时,还谨守着女人家不上桌吃饭老规矩……如今,被自家媳妇夹枪带棒地不留半点情面地把一切扒拉出来,那些她刻意遗忘的过往一一在眼前晃过,性格内向的她,终是忍不住了,她似乎要把所有的委屈与不甘借助哭声,向那棵从不言语、不能给她任何抚慰的呆物宣泄……
有关于“细媳妇”的一切已经久远,久远到那悲愤的哭诉声在我记忆里也只是隐隐约约……
三寸金莲
“哈!哈!太娭毑睡着了,这下……”我虽窃喜着,但还是习惯性的放轻了脚步。可惜,我这只瘦弱的野猫终究不是猫啊,做不到悄无声息。太娭毑垂着的脑袋微微向下一顿,花白头发轻轻向上一扬,她便迅速抬起头,用那条终年不离手的曾经是白色的手帕,揩了揩并没有流下梦涎的嘴角,“红伢子啊,来啰!到太娭毑这里来……”
“太娭毑,我不!我妈在前头喊我。”我装着很听话、很着急的样子,迈开步子准备跑。
“你这鬼崽子几,又骗太娭毑。你妈和你满婶几到黄土包去了,你以为我不晓得?”
“满婶几?”我不知何时又多了一位这样的亲戚。想了半天,该是太娭毑把她儿媳和我的辈分搞混了,所谓满婶几应该是我满娭。想是这样想,我的脚步还是未停,只想快些、再快些,逃离太娭毑的视线范围。
太娭毑依然微眯着眼睛,反手朝墙外摸索着手杖,颤巍巍地起身,恐怕是想到禾场前面的路上拦住我。
“太娭毑,您老坐下啰,等下又摔倒了怎么得了?”基于七、八年来,太娭毑时不时左一个雪枣、右一块要化了的薄荷糖的贿赂,我终究狠不下心,只好临时更改方向,奔向太娭毑。
老规矩,从满爹堂屋左边的后面那间小房间的床底下,拖出那个近乎于黑色的小木脚盆,吃力地移到太娭毑脚边,又到灶屋里用竹端子在灶台中间的瓮坛里,舀出几端子热水放脚盆里。太娭毑已经搬起她的脚,把裹脚布一层一层象剥粽子般剥开。
长长的裹脚布下肯定不是香软可口的粽子,而是一双被捆绑得变形了的脚。这双脚不再如幼时一样引起我的好奇,相反,我有些讨厌这双天天洗还是会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腐臭味的脚。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甚至愈加憎恨太娭毑那位早已作古了心事狠毒的娘亲。我的鞋子不合脚,起了几个血泡,我妈都心疼得赶嫁似的帮我做大一点的布鞋,她的娘怎么就能黑着良心把女儿的脚趾生生的反折到脚底,再用这长长的白布将它紧紧缠绕?
看着清水中那双不足二十厘米长的脚,不到十岁的我肯定不会考虑它是怎样撑起太娭毑这副躯体的,仅仅想问一下,“太娭毑,您……”
“红伢子,太娭毑跟你讲啰,太娭毑这一世啊,搭帮这双细脚几呢!”太娭毑弓着身躯,擦拭珍宝一样,轻轻擦着枯瘦的脚杆下高高隆起的脚背。又弃了面巾,用手指抠着这双不得不称之为脚的脚板,我没看清太娭毑提起这话头时,那鸡皮似的脸上是否还有红晕。
太娭毑并不是官宦、贵族家的小姐,早年家里一贫如洗,照理在地方上算是望族的太嗲嗲不至于看上除了两只木脚盆再没半点别的嫁妆的贫女,何况当时,还有不少小有资产的殷实人家的小姐私下爱慕、倾心于他。可是,她们不知晓太嗲嗲骨子里是个非常守旧、传统的汉子,别看他没有留那条长长的辫子。那些小姐们平常遇到打情骂俏般开个什么玩笑还是可以,但是选堂客,看脚可比看脸重要多了。为什么?那些小姐们受新思想影响,不顾家中母亲寻死觅活,硬把裹得差不多成型了的脚给放开了,这是不孝;她们成天用这双“解放脚”从这村窜到那村,就是不守妇道,太嗲嗲从心底就瞧不上她们。
“妹子啊,不是为娘的狠心,你不绑个小脚,以后哪会有人要你?”年幼时,太娭毑的娘亲,边死命给太娭毑紧裹脚布,边哽咽着劝正痛得大呼小叫的太娭毑忍着点。
于是,在脚还未呼吸到新鲜空气时,又被太娭毑亲手一寸一寸的紧勒住。
外面的大脚板在窗前的土路上,“噼噼啪啪”跑得灰直扑,太娭毑摇晃着走到窗前,推开窗羡慕地看着那些忙碌而欢实的身影,又摇着头关上窗,摇晃着走到绣架前,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绣着那幅大红弓鞋面。虽然那时她并不知晓他在何方、姓甚名谁,但她心底坚信着,定会有那么个人,敲锣打鼓地来接她,因为她有一双让娘亲骄傲的小脚。
我无数次看过太娭毑藏在箱底的弓鞋;无数次听过太娭毑有些得意地说起太嗲嗲是如何识货,最终娶了拥有一双细脚的她;也无数次见太娭毑抚摸着那双尖尖的红色缎面的弓鞋,叹息着“这鞋只能让我带进老屋里去啰!”虽然我不懂得“老屋”是哪里,依旧很是惊悚地把太娭毑口中的“天脚”往外挪。
在羞涩往事的回忆中,太娭毑终于清洗好她的脚,我照例掀起脚盆,把干净得只带了些味的水倒入屋檐沟,水顺着浅浅的沟向外缓缓流淌。由此,那一句“屋檐水滴到现窝里”的话,也有些不对,水都不是以前的水,窝还会是先前的窝?
冬日的阳光依旧缓缓的照着,裹好裹脚布、穿好黑色的怪模怪样的鞋子的太娭毑,没有如以前那样,突然把那双裹得怪异的脚,直直地伸到我面前,以期引发我的尖叫,换来她干瘪的嘴角那一丝上扬。她安静而祥和的微眯着眼,在难得的冬阳下享受着……
我终究没能问出:“太娭毑,您还痛吗?”
——题记
小垸清晨的雾不只是浓,还透着些诡异。
“是真的吗?那个……昨晚……”女声细声细气,仿似在浓雾极力掩盖下,探头探脑的钻出来,勾动着人们的好奇心。
几声急促的脚步声随着粗犷地男声传出,“你看罗,这么早,哪个会红口白牙的咒别个呢?哪怕是她——”他有意提高着声音,似乎想抹平一众旁观者、旁听者的好奇心。
“应该是真的啰!差不多天亮时,我听到好象哪里放了一挂‘十八响’,炸得一屁响,我是被吓醒的……”
脚步声逐渐多了起来、乱了起来,一个气息不匀的声音响起:“那是来了鬼了,平时打大炸雷都炸不醒你,一挂十八响倒把你吓醒了……昨晚上狗都冒叫几声,哪里就放鞭子了,莫呆在这里说瞎话,快些帮我抬着这口锅。”
“张家嫂子,你把这口老天锅都搬出来了,那……这事肯定是真的了。”细声细气的女声还是有些不确信。
“就早晨四、五点钟的事。哎!做孽哩!去的时候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不是我屋里当家的去借锄头,还不晓得要好久才发现……”
“啊?!她真的‘过’了?!”
“是哩!哎!”
“哎!”
“哎……”
她是村里的禁忌。传说中的她,以前原本能说会道,容貌秀丽,并不是现今流行版本中的面相狰狞的哑巴。
其实小一辈的人见过她真面目的不少,她穿着一身与她一头凌乱的白发极不相称的,洗得发白、干净整齐、连补丁也服服贴贴的灰色长袍。看见孩子们常咧开干瘪的嘴,漾出一团她自认为和善而慈祥的笑容……因此孩子们对这个形容枯槁的老妇人的恐惧远不及对她好奇心。
年少时的她应是很聪明,从未上过学堂,却可以复述整本《烈女传》里的故事;她也应该很有教养,开口“规矩”,闭口“老班子手里可不兴这样”;她应该体态轻盈,住在高处洲子时,从宽敞的木屋的阁楼下来时,无声无息;她也应该长得很是漂亮,父母给她定下的未婚夫出去前,曾经从她房前苦枣树荡到她房中,只为临别时看她一眼;她还应该是那个时代许多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如果不是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她更应该会继续成为别人眼中恪守妇道、孝顺公婆的好儿媳,贤良恭德的好妻子,温柔慈爱的好母亲……
那场变故已经很久远了,从她未婚夫黎明前从她窗子跳下,趔趄了一下,不舍地回望她一眼后,撒开脚丫子跑到湖边划着小渔划子离开苇荡时算起,将近一个世纪了。
那年,在双方父母高高兴兴地筹备他们的婚礼时,村子里有人传言,她男人在外地死了。她不信,所以依旧不紧不慢地绣着她的嫁衣,她也不知道,她那并不很深的闺房外闲言碎语正慢慢堆积,“切!还说她如何如何守规矩呢!听说那后生走之前在她房里呆了一晚,天晓得搞了些什么?这下,应验了吧!”
“我看她就是一个白虎精,要不,她那未过门的男人,可是村里最壮的后生,乍会说没就没……”
“我看啦,么子精怪都不是,她就是天上的扫把星,扫着谁,谁倒霉……”
据说,那扇对着苦枣树的窗再没打开过,但是多事的人们隐约还可以看见她坐在窗下赶嫁。
到了成亲的日子,她男人果真不在,她抱着灵位成了亲。
可是这些不为人知的惦念及惋惜并没坚持多少年,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所有情绪都转换成鄙夷、唾弃……
“天杀的!你屋里真的缺德呢,养出你这么个破烂货……来啊!大家都来看看,这个臭不要脸的都做了些什么肮脏事……”她那出了名厉害的婆婆站在牛屎糊的坪里晃动着两截稻草,泼天泼地的喊。
不得不说,人们在这方面的领悟能力是超乎寻常的,从她婆婆那随唾沫星子横飞的恶言恶语中,他们运用有限的词汇拼成了一个又一个伤风败俗、违背伦理道德的故事。
婆婆怕年青的媳妇守不住,每晚等儿媳吹灯入睡后,偷偷在前门、后门系根稻草做记号,清早婆婆第一件事就是前后察看稻草是否完好无损。
这天婆婆发现后门口的稻草断成两截,便怒气冲冲地责问儿媳。儿媳很是不解,甚至委屈得不行,面对恶语交加的婆婆,她只能哽咽着申诉:“我昨晚拉肚子,到外面茅厕去了一趟……”然后泪如雨下、不再言语。
公公可能深知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或者是怜惜儿媳年纪轻轻就守寡的苦楚,出言调解:“昨晚的菜怕是真有问题,我半夜时分也起来了一回……”
婆婆一听,“腾”地跳起三尺高,双眼喷火似地,颤抖着手指,指着公公,“你们、你们……”许是气极,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只好恨恨地放下手,转而又跳起脚来,狠狠赏了儿媳一记耳光,再然后……
然后,她的房间前后都被上了锁,钥匙就挂在婆婆肥胖的腰间日夜不离。她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却又被人们的闲言碎语中勾勒着……当然,幽居的她还是如未嫁时一样,凭一扇纸窗、一堵芦墙阻挡着外面妇人们的啐出的浓痰、口水,男人们肆意下作的编派、臆想。
好些年过去了,终有人还是觉着她可怜,跑到她娘家,动员她父亲及兄长把她接回家,说是现在是新中国、新时代了,不时兴老班子那一套,不如让她回来再另行婚配。她父亲仰天长叹:“哎!我有什么办法呢?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这都是她的命!是她自己造的孽!”
嫂子在大门外泪眼婆娑,回房与丈夫商量,把自己未满三岁的小儿子过继给她,也让她以后有个依靠。
孩子从此喊这个明明住得很近,却从未谋过面的姑姑作娘。如同嫂子所想,她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生命般珍爱疼惜。直至五年后,孩子贪玩,欺侮足不能出户的娘,跑到外面玩到晚饭时分还未归家,等婆婆、公公在屋旁打不湿牛背的小水塘里把孩子抱上来时,小小身躯已经浮肿、冰凉。
嫂子闻讯后,早已哭晕在家,兄长自她嫁后第二次登门,红着眼指着她鼻子咆哮着扔下一句话:“从此,你和我再无牵连……”她抱着孩子不哭也不闹,人们对她的指责又增添了无数条,诸如冷血、恶毒、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的……
突然有一天,年近七十的婆婆厌倦了每日每夜单调而又重复的“嗡、嗡、嗡”的纺纱声,让人在村里一片树林间搭了一个小茅屋,把她连人带纺车丢了进去。
孤苦几十年后,这些送她最后一程而忙碌的人群中,有好几代是在年幼时,被长辈们用她的名字吓大的;有好几辈新媳妇在新婚时,认认真真接受各自母亲、婆婆垂训时,必定听到过一句,“我再三告诫你,千万莫学她的样……”
而今她悄无声息地走了,比她年长两岁的兄长颤颤微微、老泪纵横地抚着薄薄地棺木,一声一声的重复着,“老妹啊!是哥哥对不住你啊……”悲痛中的哥哥定是想不出对不住她的原因;他也定然不知道父母故去前是否对这苦命的老妹有所惦念,如同他不知道静静地躺在枕棺木里的她的老妹现今的模样。他或许和队上所有老的、少的一样,只记得传说中她年少时的美丽,只记得伴随她一生的代名词,“那个守望门寡的……”甚至……,这些对她都不重要了,她只是静静地、静静地在等待他们将她掩埋……
借种
眼看就要年关,喜儿妈妈这几天急得嘴角都生着流星泡,一双脚更是在村里煤渣路上两头奔。爬过年埂子的正月初四,她的满女,喜儿要出嫁了。俗话说,‘爷一满崽,嗲一长孙。’这都是放在心尖尖上的人,做娘的呢?自然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家屋里满妹子,还不说这喜儿虽然从小看得娇,可她受得起,她比一般孩子听话,而且很勤快,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说,只说到苇山砍芦苇,她哪年不得赚个两、三百?喜儿妈在男方介绍人上门时,就含着不知怎么出来的眼泪打过包票:“我喜儿出嫁时,一定赶全大队最好的给她,还要给她做两皮箱新衣服……”
这不,弹出嫁被窝的弹匠已进屋十多天,两担大木笼子和一个当得半间屋的大什柜,已放在横屋里等漆匠刷第三遍朱红漆,就连出嫁酒那天烧茶要用的甜酒,喜儿妈都拍了两窝,只是,只是……让喜儿妈烦心的是,裁缝师傅都喊没空。
也怪不得别人,明年年头年尾都是春,结婚、定婚的本就多,加上今年冬天特别冷,老人、孩子那些穿了好些年,或者穿过几代人的油光放亮、补丁叠补丁的棉衣、夹袄早就该换了,趁着收成好,还不得赶紧做几件新的过年?如此上门裁缝便紧俏起来,这家还没出屋,那家便来喊,手艺好的更加挤档不进。
“哦唷!你这鬼婆子又窜得哪里去呢?只看见你一双脚翻羊叉一样不歇半点气。”庚嫂子抓着一把炒得黑不溜秋的蚕豆,边嚼边拦住喜儿妈。
“莫管起这个事,管起我就脑壳痛。我呀,去东头看看,问一下训珍嫂子,她那个会做衣的妹子抽得空出不,想接她来帮我满女做嫁衣。”
“什么?你找她?还接她做嫁衣?你也几十岁的人了,不晓得忌讳一点。”庚嫂子从灰色大罩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铁菱角一样的蚕豆,硬塞给喜儿妈。
“忌讳什么?听人讲,她手艺蛮好的!去年她给我家喜儿做了件白竹布褂子,肩是肩、腰是腰的,喜儿穿得变了颜色还在穿……忌讳什么?”昨晚,喜儿见妈妈望着码在床上的几匹布发愁,知道这一段裁缝师傅难请,便跟妈妈说,“训珍婶婶家那个美姣阿姨做的衣服我蛮爱的,要不,去请她?”喜儿妈一听,拍了拍后脑勺,暗自责怪自己急晕了头,只看到本场这几个人,不晓得外面大垸子里还有许多能人巧匠。
“忌讳什么?你是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那训珍婆娘看见她妹子就念个不停,‘我这妹子长是长得乖,可中看不中用呢!结婚三、四年了,疖子都冇看见她生一个,哎!’我听说啊……”庚嫂子四下张望一番,把喜儿妈拖到屋檐下,神神秘秘地说了起来。
印象中美姣长相十分标致。每次到苇场来做衣服,村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事没事地经过主家屋,只为偷偷瞄她几眼。村里德高望重的大嗲看过她后,回家曾悄悄对孙子说,“这个美姣啊,扮花鼓戏里的妹子不要化妆了。你看啰,该白的地方白,该红的地方红,眉毛、辫子青得炭一样……”
她婚后第二年,婆婆见她肚子老是鼓不起,以为她是“石女”,等她上完厕所后,悄悄观察她有没有小日子,也暗自向自家儿子打探过,小两口的闺房之事。过一段时间后,婆婆自认为一切妥当,只好边给她吃各种不知从哪里打听来的单方的同时,还亲自向她传授一些不知有没有用的易受孕之法。她红着脸应下,可是一年很快过去,她的肚子还是扁平扁平。婆婆忍不住了,堂而皇之地跑到她娘家打探,问她母亲是结婚多久才生子?她已出嫁的三个姐姐又是什么时候破生?嫂子又是什么时候怀的孕?甚至还问她的两个妹子那个正不正常?婆婆把那莫须有的家族遗传排除后,又到处向人打听,她未嫁时作风是不是有问题。乡下有许多大姑娘与人苟合后,珠胎暗结时,胡乱打胎,以至婚后不孕不育的大有人在。这女人怀或生一胎后再也无法受孕的现象他们叫“秤砣生”,她怕美姣刚好是其中一个。
美姣虽然觉得委曲,也强忍着。她认定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怕别人胡乱猜疑,再说她到底是不是黄花闺女,她丈夫最清楚。只要他不说什么,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这样在苦水中又泡过去一年,她的肚子并没有被那些药水泡大。
美姣开始心虚了,怕面对公公婆婆,尤其怕遇上他们询问的眼神。每天做完事,累得拖脚软手,进门时还不忘用余光看看他们在没在,不在便长吁一口气,快速走进自己的房间;如果在,便深埋着头,一步一挨。就连把做衣赚的工钱交给婆婆时也小心翼翼看她的脸色。她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夫家所有人了,本以为女人生孩子就像母鸡生蛋般容易,不曾想在她身上却是如此艰难。
渐渐地家中再也没有她清亮的笑声;渐渐地她的话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她只用“嗯、啊”表示听到或者没听清。
在娘家时,美姣与三姐训珍关系就比二姐她们亲。训珍每隔一段时间,便以人家请美姣做衣服为由,接她到苇场住几天。在苇场的日子便是她难得的轻松之时。
训珍先前也怪亲家娘太性急,她认为不是每对新婚夫妇都是“上门喜”,好多也是结婚一年半载后才有好消息的,再说得子或得女,全靠祖宗庇佑,急是急不来的。她也用这一套劝着美姣,可一晃三年过去了,显然这些理由站不稳脚。虽然在亲家娘指桑骂槐的骂自家屋里老母鸡:“喂着你又不生蛋,喂你有什么用?”或者干脆明的指着美姣骂:“老娘喂只鸡公子不晓生蛋还做得过年砵子,不晓得我崽娶你有什么卵用?……”之类的话时,她跳起脚来与之对骂过,“你们添不添孙与我妹子何干?是你们祖上无德……”但是作为过来人,她知道其间肯定有问题,不是自家妹子不争气便是妹夫无寸用。便悄悄劝美姣,让她带老公一起到县城去检查看看,到时有病治病,无病便两人商量,过得下去便过,过不下去好合好散,怎么样也好过时时受这冤枉气。
美姣其实自己也想过许多办法,算八字拜菩萨,听一样信一样,都说她命里是“先开花后结果”。可是一年一年过去,送子娘娘并没有给她期待中的那个乖巧可爱的女儿。她听从了三姐的话,最主要的是不忍心看六、七十岁的父母,天天防备婆婆时不时的上审。到晚上便跟丈夫挑明,“要不,我们去检查一下,或许医院有办法,让我们生一男半女,也省得每天这样土地公对土地婆一样,我干对着你,你干对着我……”她满脸希冀的憧憬着。丈夫却沉默不语,很久以后,才对她说:“靠我肯定是空的了。不如你去借种,你想一下看,我的兄弟姐妹家的男的,你愿意跟哪个?只要你说,我就是下跪求也把他们求来……你放心,只要我不说,你不说,他占了便宜的更不会说,我爷娘自然就不会晓得……”
美姣听他这么一说,如同被雷击中。原来,他一直知道原因在他,可是他却伙同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指责、辱骂于她,甚至两人过夫妻生活时,还以此为借口对她百般凌辱、折磨……这也罢了,日子再苦熬熬就过去了,如今,他竟出了这样一个无耻的荒唐主意,“老天啊……”她掩面痛哭不已。
“你不晓得吧,我就晓得她这种人要好风骚便好风骚……先不管这个,只说她没生这一点,你还找她跟满妹子做嫁衣?你看我能干吧?能干有什么用?就因我没生儿子,别人不但骂我‘绝代种’,什么好事都轮不上我,就连钉嫁字被窝也不让我拢边,说是非得请儿女双全的人……你啊你!还不信邪,去请她……”庚嫂子一气说下来,两边嘴角泛白,不知是唾沫星子还是粘着蚕豆渣子。
“还有这样的事?你看可怜不啰!一个乖乖洁洁的妹几何解一个这样的命……”喜儿妈轻叹一口气后,马上又想到喜儿的嫁衣还是没有着落,又“啪!啪!啪!”走远了。
指责也好,猜疑也好;同情也罢,怜惜也罢。远在大垸深处的美姣是不在乎了。她疯了,就在她大伯子打开房门,她丈夫怨恨地走出房门那一刻,便疯了。都说她疯得与常人不同,她发作起来一不打人二不骂人。只是看见不得别人家的小毛毛,看见了便一把夺过,死命抱在怀里,扒开孩子的裤,咬他们胖乎乎的小屁股,边咬边流泪,好像痛的是她。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