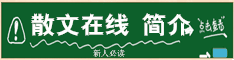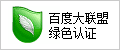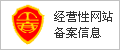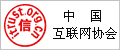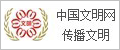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我的军营,穿越在时光隧道
文/镜台无尘
2021年12月初,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上午,我坐在冬阳普照的草地上,眯缝着双眼,正与一帮老家伙下象棋。电话响了,接到单位通知:本月11号,全体干部职工包括离退休人员进行年度体检。
体检,是福利,体现了组织的关怀呵护。
体检,是哨兵,按时且忠诚地守护着我们的身体。一有情况,便吹响口哨,发出警报,使我们及时应诊对症下药。我的胆结石,我的冠心病,都是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探测出来的,继而到医院就诊复查并有效治疗。
两年一次的常规体检,已成惯例。
凡成惯例的事物,容易养成一种豁达洒脱的态性,轻松而来,谈笑而去,情绪如明镜般的榕湖水,波澜不惊,风平浪静。每次体检结束后,在等待检查结果的半月或30天中,既不期期艾艾地焦虑,亦无惶惶恐恐之猜忌。
按照指定的日期地点,于早上8点,我走进桂林181医院(现为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924医院)。目标:三楼体检中心。
我站在大厅驻足四望,科室间,楼道上,三三两两的白大褂、迷彩服来来去去,穿梭而过。我窥探,那白大褂的领口处露出了绿色的军装;我猜测,穿迷彩服的就是看病或住院的军人。这不是医院吗,眼前的人形身影怎么是那般的急促与矫健?我当然知道,军人,不管在哪里,行似风,坐如钟,站是松,这是军人的作风!
大厅荧光屏上“一切为打仗!”“一切为官兵”的标语,迎面而来;
“军人取药处”“军人挂号窗”“军人就诊室”的门匾与标牌,光彩夺目。
身临其境,耳濡目染,是亲切?还是陌生?想拥抱,却又胆怯。
我似乎听到,隐隐约约的军号声从遥远的天际响起;我彷佛看到,在红彤彤的旭日映照下,操场中心的旗杆高处,那面像火焰般舞动的军旗,随风招展,猎猎作响。刹那间,我眼前出现五颜六色的光环,交织闪烁不停跳动,我眼花瞭乱,一脚踏空,蓦地跌进一条幽深的隧道……
我在这隧道里飞快滑行着,浮光掠影,云蒸霞蔚,烟雾缭绕。那一桩桩前尘影事,时聚时散;那一个个战友兄弟,似湮似烁。哦,我穿越在传说的时光隧道里,追寻那早已离别但又魂牵梦绕的军营……
朦胧中,传来一声严厉的呵斥:“喊什么喊!你看看人家,一声都不吭!”
我吓了一跳,睁开紧闭的双眼,朝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几米远的那架手术台上的病人,正在做手术。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只见他痛得忍不住嚎叫起来,被医生的这一呵斥,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极度压抑、断断续续的嗡嗡呢喃。
“你别乱动!”这是面前的医生对我说的,“不要看那边。”随即,一只温软的手把我偏侧着的脑袋扶正过来。这时,我看到了一双垂泪的眼睛,啊,她在为我流泪吗?我在感动的同时也莫名其妙!这是一位满脸稚气的小护士,她坐在我身旁的凳上,负责我的手臂不动。其实,我的手腕在手术前就已被绑定。开始动刀的时候,医生说,这是半麻,有点痛,闭上眼,要忍住。医生一字一顿,我便一顿一点头。
“这是半麻。”
“嗯”我点一下头,看住医生。
“有点痛。”
“哦”我点一下头,不敢看医生。
“闭上眼。”
我马上把双眼闭了。
“要忍住!”
我上下牙齿磕了一下,算是回答。
“别紧张。”医生见我在抖,补上一句。
我发出抖音:嗯,不不不紧张。
紧闭双眼,什么都不看,任凭医生和护士们在周围忙碌。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我,一进了这手术室里,就全身发冷,颤抖起来,我干吗好好的要挨刀子?我暗暗叹了一声,怪谁?这不是我自找的嘛!
这是一九七一年夏季的一天,我奉令调到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报到那天,从看守坪石监狱的老连队赶火车到韶关,转班车到黄岗,然后,步行五公里至团部驻地,赤日当头,大汗淋淋,军衣与背包都被汗水浸湿。走进宣传股,向股长敬礼后,与办公室内的几位前辈一一握手。握过手后发现他们的神情有些别扭,有人不停地擤起鼻子来。我马上意识到,是我的腋臭,在炎热与汗水的泡制中,散发出更加浓烈的臭气,这臭气熏了大家。我尴尬地说,不好意思,我有狐臭。股长和同事们似笑非笑地说,没事没事。接下来的日子,好几次被宣传股的领导和同事打趣嘲笑,虽无恶意,只是拿我这个新来的小老弟开开玩笑罢了。但我年轻气盛,却又自惭形秽,俗话说,士可杀不可侮!一气之下,请假看病,昂首踏进了广州军区一九七医院。
那门诊医生惊愕地瞪着我,你说什么?要割腋臭?!
我斩钉截铁回答:是的。臭不可闻,不割不得安身。不信您闻闻。我掀开衣服,凑了过去。
那医生忙不迭地站起来往后退,连声说,得得得,不闻了。我带你去找院长。
我愣了一会,问他,不是个小手术吗,还要惊动院长大人?
他说,你既不是军事训练伤了筋骨,也非坑道塌方压断手脚,连常见的呕吐拉稀肠胃闹病都不是,凭什么要住院挨刀?你这种可做可不做的手术,我可做不了主,必须要院长亲自定。
到了院长室,一位满头花白的老军医上下打量了我几秒钟,然后绷着脸严肃着说,知道不,这腋臭手术属于美容了。你这年青人很爱美呀。
我涨红了脸,急不择语地辩解,院长,我的科长和同事嫌我臭,您也取笑我?!
院长的脸色平和开来,说道,好了,小同志,不要紧张。做了也好,免得妨碍他人。来,让我看看。
我走到院长面前立定,他弯下腰扭着头,把鼻子伸过来闻了闻我的腋窝,顿时,眉毛胡子挤成一堆,偏开脑袋吐出一口唾沫,说道:嗯——够味!实在够味!
看到院长走开,我着急了,举起另一只手臂,说,院长,这个更臭,您再闻闻。院长摆摆手,在桌前坐下,说,行了,不用闻了。
我一脸失望地盯着院长,欲言又罢,眼眶涌出不争气的泪水。
院长看我着急的样子,竟然呵呵大笑起来。笑毕,大笔一挥,割!
于是,我住院的第二天上午便安排了手术。
记得一大早,两个护士推着平车来到我的病床边,说,上来吧。
我说,不用。我没病没痛,好好的,干吗要躺这上面?
护士说,谁做手术都这样。这是规定。
我盯着这架铺着暗绿色布单的平车,好像看到了先前无数个在这上面躺过的人体,一阵恶心。我一把推开车子,说,前面带路。我能走。
两个护士互相对视了一下,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就走吧。一个护士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她的后面,另一个护士推着空空的平车,跟在我的后面。迎着病房和走廊上各种目光,一起向手术室走去。
一进手术室,正忙碌着的医生和护士停下手中的工作,齐唰唰地看着我,又看看空着的平车,他们的表情里既有一丝不解又带些许滑稽。我手足无措地看了看这群人,这么多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我很不自在,畏畏缩缩,不敢乱语。
面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就像布满刑具的审讯室。偌大的空间里,门窗紧闭,空调的暖气开着,排气扇时快时慢地转动,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天花板上吊着莲花形状的无影灯,四面墙壁装着搁板和高矮立柜,墙上挂着各式的医疗器具,室内共两架手术台,那张台上已躺了一个人。
静默中,一个医生呵呵几声,说,这小子现在活蹦乱跳的,等会就要挨刀,可别拉稀。其他的人跟着笑起来。室内气氛活动开来。 “行啊自己走来的。”一位中年模样、穿着暗绿色工作服的医生指着一张手术台说,“也自己上去吧?”
我几步跨到台前,像猴一样往上一窜,身子便躺了上去。
医生和护士围过来,拉的拉,扯的扯,一会功夫,我的身子在手术台上摆成十字形,两只手腕被布带固定在特制的木条上,脖子以下盖着厚重的暗绿色的布,我看不到自己的躯干肢体。我心里暗暗伤心:奶奶的,我这是准备受刑了?
医生解释说,我的创口位置在两边的腋窝,在切割腋腺皮肉时,不能有丝毫的动弹的。所以,我的手腕和腰部必须固定好。
不知是麻醉不到位,还是麻药效果不好,像是有人在活生生割我腋窝里的皮肉,那种疼,一辈子刻骨铭心。每一刀划下去,我便要受一次巨痛。我一次又一次想大声喊停!不做了,纵使我的腋臭熏翻全人类,我也顾不上了!
可是这个“停”字我喊不出口,做事,最怕半途而废。胜利,往往在最后的坚持之中。痛就痛,总不至于死人吧!只要死不了,前面是刀山火海,闯他一回又如何!
我双目紧闭,五官扭曲,牙齿咬住下唇,齿尖刺进肉里,咬破了嘴唇,鲜血流出来。这红红的血液流到唇下漫漫散开,攻城略地,浸染了我的下巴和脖子。事后,那位小护士告诉我,看见你的样子,又恐怖又可怜。我说,所以,你就哭了?新兵小丫头吧?以后,见多了各种血淋淋的场景,你就心硬了。呵!
像小护士这样的大院子弟,在当年,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没书读,而且要到农村插队,于是,很多团职以上直到将军的高干子女被送进了部队。这些人,与基层连队里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相比,无论风度还是谈吐,都显得格外不同。而且年龄都偏小。如小护士,就只有十四五岁。她的父亲放牛娃当兵,戎马倥偬,战功累累,却是大老粗一个。她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温婉贤淑。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兴起扫盲运动,她,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走进部队,任文化教员。没多久,在组织安排下,她与时任团长的小护士父亲组成革命家庭,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婴——就是眼前的这位小护士。从团部到军区机关的部队大院,戒备森严,与世隔绝,在这风雨无恙的避风港里,养尊处优,无忧无虑,没经历过穷孩子们的痛苦与折磨。小护士的性格里,继承了母亲弱不经风、多愁善感的基因,见不得世间的残酷与冷漠。
医院里的一切作息,都按军队条例执行,起床号,开饭号,熄灯号,到点就响。能动弹行走的病号必须闻号则起,不准赖床。住院一个多星期,却没听到冲锋号和紧急集合号,估计这两号医院用不上。想想也是,如果医院里吹起冲锋号,那岂不是鸡飞狗跳连滚带爬一派乱相?!
晚上十点熄灯。我睡不着,就带一本书到食堂去看。食堂可以开灯的。
那年头,在部队看病住院,一律不要钱。在医院食堂吃饭,干部一顿只交1毛或2毛钱,如果没有带钱,就记上账,什么时候来把钱还上都可以。战士则不须交纳伙食费,你想吃多少就使劲造吧,没人笑你。病人吃的都是营养餐,也叫病号饭,鸡鸭鱼肉蛋,任选。凡住院者,不完全好利索,一般不允许出院——当然,那种为躲避军事训练或战备施工的苦累而借病住院的个别人,则另当别论。
腋术,在今天看来,是个不起眼的微创手术,在门诊就能做。可在当年,为了除臭务尽,要割开一个大口子,挖出里面的臭根腺源。如果麻醉的效果不好的话,简直是生割活剥,会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我经历了这场痛不欲生的手术,把皮肉里的汗腺组织都切了个一干二净,掏得个清清爽爽。缝合时,因为创口面大,只能把周边的皮肤拉过来拼拢。手术后,两腋窝处各有一条10多厘米长的伤口,怕伤口裂开,双肩扎了很厚的绷带并上了固定扎板,大臂叉开不能动弹,小臂悬在半空,成天晃荡。
在病房呆了一个多星期,伤口还没完全愈合,我归队心切,趁护士不注意,取下针头,扯掉了绷带,偷偷逃离了医院。
回到团里后,每天都要去卫生队换药打针,半个月后才拆线。每天早上起来抬手锻练。刚开始,手臂只能持平,不能上举,经过两个月的活动后才勉强举过头顶。我的手术做得彻底,臭气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左右腋下各有一条像百脚虫形状的疤痕——这是那次手术的唯一纪念物。
几十年过去,医疗技术和设备已鸟枪换炮更新换代了。现在去医院切除腋臭,只是一个小小的微创,在门诊就做了,不到半小时可自行回家。不过,听说现在的微创手术,效果并不好,除恶不尽,遗臭无穷呀。呵!
(注:文中关于往事的记叙来自我当年的日记,并非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