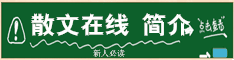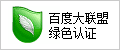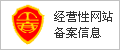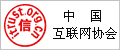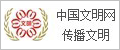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1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几岁大的时候,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桑树,挺拔苍翠,粗壮的旁枝凌生于老屋上方。常在夏日的黄昏时分,避开父母,相约一两玩伴,猴儿一样嬉闹着盘上树冠,再顺着颤悠悠的树枝溜到屋面上去。脱去了鞋子的脚丫踩在树影斑驳平坦的屋顶,清凉的晚风中,沉实的房礁散发出阳光的余热,从脚底涌入幼小的身体,涌入那时懵懂单纯的心中,那是难以言喻的惬意与温暖。那一刻,感觉无声的老屋房顶就像是母亲的怀抱,在默默地给我幸福与安宁。沐浴遥远天际落日的余晖,听闻树叶悦耳的沙沙声,平铺了身体,就这样无声地仰视着,看瓦蓝色高远的天空中,那朵朵洁白变幻的云彩,看从水草茂盛的河流中来体型硕大的鹈鹕,慢悠悠飞进又滑出视野。偶有一两枚被土雀啄落的桑树叶子,乘着晚风旋上面颊,那浓郁的桑木气息,虽历经多年,依然在肺腑中充盈。可以说,就是从那时起,藉由这树、这屋,才认定身边的世界是如此斑斓而美丽的。 在我眼中,乡村的每一栋房子都具有生命,无声却蓬勃。它们已经成为时光的见证和守望者,古朴纯粹,一世安然。和很多别的乡村孩娃一样,我也是在老屋的注视与怀抱中慢慢长大。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心中有那样一间房子,还是在乳臭未干时,它就和我的血脉、心跳联系在一起,和泥土、树木联系在一起,和母亲的顶针、父亲的旱烟联系在一起。那是收拢了风、庄稼、河流、日月星辰,家人全部的欢笑与泪水的一间房子,是最初的我的摇篮我的梦。直到如今,从它窗口递出的那盏油灯,昏黄却温馨的灯火依然照亮着我的内心,照亮着我脚下的道路。 2 最初,村人的住宅以泥坯草房为主,高大挺阔,尖顶巍峨,除此很少见不同的样式。这种房子沿袭了固有的传统格局,坐北朝南、分三间,东西走向的屋子,南面的炕。东房间为正间,西房间为偏间,正、偏间都是住人的所在,按现在人的习惯叫法是卧室。正居中的一间称为“当屋”,也有些地方叫“堂屋”的。“当屋”的功用有两个,一是做了简易的厨房和餐厅;再就是前后门大敞四开,任由天风、飞鸟、邻里街坊或是过路的随意穿行。当时的民风淳朴,乡人基本日不闭户,为了抄近路而肆意穿他人堂而过,甚至一时口渴不征得主人同意,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水仰脖儿就喝的行为是被默许的,已然见怪不怪了。到了用餐时间,在相互交织弥漫的食物香气里,梁间燕窝雏鸟的唧唧声中,前后几进的人家,团团围坐在餐桌旁隔屋相望,互相举杯致意。又每有顽皮的孩子得到叔伯婶娘的邀请,雀儿一样在各个“当屋”中跑来跑去,引发阵阵欢欣的笑声,那场景现在想来还如许温馨。一度,“当屋”成为连接起千家万户的敞亮纽带,成为浓浓乡情的独特象征。 草房一般高大,稳固起见,地基要深挖,用夯夯实,拿青砖或石头涂抹灰泥垒成“旋拱”。那拱类似于桥拱。先将打实的地面削出自然流畅的弧坡,再以砖块或石头于其上严密拼接成两米长短的数重半圆形状,几十个这样的“旋拱”沿墙基相连分布,凝固的波浪相似,上用沙灰覆盖,拍实、找平之后就可以垒砌墙壁了。草房的墙壁从底到顶多用土坯,有些人家还要在墙壁中间支几根立木,以增加墙壁负重能力,不过这种形式并不多见。砌墙中间,需知会木工,将门窗框镶入,不可马虎。草房的梁架多为三角架结构,主、侧梁一般使用松木,最以陈年落叶松为优,并去皮后涂以桐油。椽木却往往马虎,普通的槐树枝杈即可,唯有杨木因其承重力差、易弯折的缺陷而不被使用。于侧梁间自下而上铺设椽子至主木,铁钉钉牢。完成后的梁架就像一具奇形骨架,尽显嶙峋峻砺,恍似悬空耸起的穿风之阁;又或是于半空竖起了一架架散发树木清香的梯子,通向灿烂阳光。 梁架铺设完毕,将秫秸根梢切齐,编成能经得住人来回行走的“雹子”蒙在梁架上,用掺进了新鲜麦秸的“菜泥”覆盖抹平,这叫“上粑泥”。接下来,就是苫房的环节了。在家乡,给草房苫盖屋顶的草多是芦苇。将经过择选的苇子编成厚实紧密的联子,卷成一束,十几个人一起发力,拖地拖举地举,运到屋顶一侧,齐发一声喊,骨碌碌地抖开铺设在房雹上,再由手艺高超的“把头”跨坐在房脊上,两手翻飞着拧出连接苇联的脊拱。远远看去,晚照夕霞中坐上脊拱的“把头”,就像是乘骑在一条昂然欲飞的长龙身上,而他身下的那随风而起的片片苇叶儿,已恍然变成了闪闪发亮的羽毛与鳞甲。在那一刻,人是欢乐的,房子是活过来的。 俗话说“一间屋子半间炕”,由此可见一铺大炕在房屋中所占的体积。乡人的炕无一例外用泥坯搭建,坯块顺倾斜地势,从各种角度相互交叠码砌,中间留出纵横相连的烟道,做出迷宫形态的同时充分展示力学原理。一铺优质大炕,必是保温舒适坚久而实用。此等炕铺,炕面用细沙灰抹平,上糊报纸,再覆以苇席。炕沿帮多用青砖,炕沿为整棵臭椿取最大直径板材,两端嵌入墙壁,时日再久,不弯不裂不走形。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的说法,人口正当繁盛,每户人家都是孩娃成群,而土炕却用它的阔大和坚实为他们打造出了一方梦风梦雨的自由天地。在我看来,幼儿时期的土炕,已不再仅是供人休憩的泥土砌成的平台。那其实是来自大地母亲地托举,是孕育着人类生命的原始子宫,有多少人是从一铺温暖的大炕开始步入自己或精彩或平淡的人生。在土炕上诞生、死去,谁都不曾真的离开土地。 整体框架完成后,安门、窗扇,熬浆糊糊窗棂纸,吊顶棚。用细黄土拌以谷壳,加水和成“菜泥”,涂抹在内外墙面。讲究些的人家,将白灰块放进一只盛满清水的大锅,淋开后,取其灰水,拿笤帚蘸水刷墙,待干后,粘贴从集市上购回的杨柳青年画。便可摆放橱柜、被褥等物举家迁进新居了。对普通的农家而言,这是一个盛大的日子,左邻右舍齐来道贺,或提鸡或牵羊或只以一张笑脸和真挚的祝福送上贺礼,主人家早已预备下流水酒席,凡来者一概不拒,那喧扬与热烈竟日不息。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梦的终圆,一个理想的实现了。 草房的建造从很早开始,那几乎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天命和召唤,由筹划、预备到付诸实施常常要耗费很多人几年甚至一生的时间。首先,它是一所矗立在人们心里的房子,你无数次在梦里勾勒它的样子,为它设计最完美的蓝图,包括每一粒沙土、每一个细节。它就像是一个虚拟中的瓶子,你不断地将它打破再加以拼接,这个循环推翻重建的过程那么令人激动、幸福和充满期待,以至于你在想象中就已得到满足,为此你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付出所有,为此你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一间旷野荒原上的房屋,向着阳光、青草敞开所有门窗。即便最终你并没有实现它的机会,你也并不曾感到遗憾,因为你有过那个梦,那个不世出的房屋便永远都在,它矗立在了你的生命中。 现实中房屋的建造同样是件大事,各种建材的准备并不比想象中的规划来得晚。事先请端了罗盘的风水先生选好房址,从几近干涸的河床挖回极具粘性的河泥堆在平坦宽阔的打谷场,用钉耙和挠钩过篦子一样来回梳理,除去其中的树枝、石块、腐败的水草等杂物(这其间,如果韧性很足的泥团里出现了四处乱钻的泥鳅或是活的河蚌,就是一件很吉利的事了,预示着连年有余后代兴旺,主人家是需要放鞭炮庆贺并拿出点心犒赏帮工人的。),赤脚上去踩得稀烂粘稠。按照固定比例拌进撕成绺的熟麻皮,以增加成坯的牢固度。铁锹铲起这样的熟泥,扣在一个放在地面上尺许见方的木制模具里,瓦刀推严抹平。取出模具后再继续下一个。经过近半月的风干蒸晒,泥坯被逐块收集起来,运回到房址的近旁,用干蒲草扎一个锥形很厚的帘子苫盖起来。一般建一间标准规格的草房,需要这样的土坯几千块,劳动量是十分惊人的。乡间有“脱坯三天不下炕,打夯累出白毛汗”的说法,其中一句感慨的就是这个了。由此可知,在那时的家乡,建造一间房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木匠师傅开始破木。我记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原木剥皮。通常情形下,做檩梁的原木基本是半年前便浸泡在水里的,为的是增强檩梁的柔韧性,而做门窗家具的原木却无需如此。给湿木剥皮很容易,不必花费很大的力气,只用一把镰刀,树皮便被半张半张地剥下来,那情形就像是随手掰开了橘子皮一样。干木头便困难多了,常常耗费掉木匠师傅大半天的时间。剥过皮的干木头经过测量在上面弹出墨线,木匠叫来徒弟,两个人用一把大锯咯吱咯吱将木头沿线锯开,破成一块块散发出植物清香的木板,再破成窗棂、窗框的原始样貌。然后,木匠师傅将这些原始构件放上长条凳,前面顶以锤死在凳面的木块,他站在长凳后面,身体涌动的波浪一样一起一伏,用刨子反反复复推刨。直到它们的表面光滑如镜,脚下团成卷状的刨花堆了一层时,他才直起身子,将夹在耳朵上的小半截铅笔取下来,在需要凿出榫槽、锯出榫头的地方画出标记。拿一把凿子对准位置,锤子敲打在凿柄上,力量轻重适度,很快的,一只只不见破茬儿的榫孔被剜了出来;再以小锯锯出不同形状的榫头。榫孔与榫头对接相扣,往往严丝合缝不见破绽,一扇窗户或是木门由此成形。按照规律,只有木匠等泥瓦匠,没有泥瓦匠等木匠的道理,因此,木匠需要在房子盖起之前做好自己的营生,这也算是不成文的行规。 土坯、门窗、檩梁都已准备就绪,正式建房的那天是精心选择的黄道吉日,祭先祖,燃放鞭炮,然后破土动工。那时候,为了减省费用,人们通常不会聘请正规的瓦匠班子,而是乡里邻居互相帮衬,由村中精通瓦工的成手坐阵指挥,监督进度质量,凡做过几天瓦匠的“二把刀”都可充作主力。而自愿前来帮忙的,不论老幼男女,不等分派,已搬坯运泥忙成一团。主家只需给这些帮工供应饭食即可,这叫做“庆工”。所以要谓之庆,在我想来,大概是当时的乡人们拿建房当了节日看待吧。 祖父的老屋就是以“庆工”的方式翻建起来的,我有幸见过那热烈的场景。破土动工选择在了春季,从此,这个万物苏萌生机勃勃的春天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再也不曾离去。自愿前来的人们很自然地分成三个梯队,有瓦工经验的人负责砌“旋拱”、墙壁、上梁、苫房草,缺乏手艺但有把子力气的男人和泥、搬土坯、搭脚手板打下手,女人和半大小子们穿梭着送来开水、点心。人们的欢笑声、上梁时的号子声、树枝上鸟儿的歌唱声交织成一首深情厚重的乡歌,回荡在那年故乡的天空,回荡在我今生的梦里、心头。 由于人手充足,加上并不要求精致,一间房子通常只用三两天的时间便可竣成。所有环节中,唯有上梁却是马虎不得的,同样需要放鞭炮,在主梁上系红布,卯铜钱,以示虔诚和吉祥。至于抹墙面砌地砖等杂活,便往往囫囵吞枣、一蹴而就了。这样的房子虽然简陋,却冬暖夏凉,温心养性。因它的全部组件都来自土地,它便是具有了博大生机的房子,会呼吸、摇曳、歌唱的房子。置身在这样的房子中,人是贴近了自然的,走进了自己内心的。 到了后来,泥坯房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红砖墙、礁子顶的更牢固美观的平房。有些富起来的人家,甚至在更敞亮的地段盖起了浑身洋气的二层小楼。人们也不再以“庆工”作为建房的首选,而是聘请专业的建筑公司,无论是设计还是建材都是越来越精益求精了。然而,那曾经的老房子却依然矗立在光阴的长河里,并不曾坍塌。它带给我的淳朴、温馨的感觉永远都在,带给我的浓浓的乡情永远都在。 3 时常回想起在老屋中的那些尘烟往事。在那些年里,通常天还没亮,站在墙头上的公鸡刚刚发出“喔喔”的啼声,母亲已经摸黑起来,摸索着划着火柴,点亮一盏放在炕沿上的油灯,用一只手小心翼翼遮拢了桔黄色跳动的火焰,掀开里屋间的土布门帘,轻手轻脚进到“当屋”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过后,传出锅盖支放在灶台上、从水缸里舀水一勺勺倾在八沿大锅里的声音,然后是“吱呀”的一声,那是她取下门闩,拉开“当屋”沉重的木门走到漆黑的院子里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伴随着由远而近有意压低的脚步声,耳朵里响起干秫秸叶子扫碰在门框上哗啦啦的声音。接下来是掏灶灰、引火、助燃的吹气声,以及高粱瓤子扎成的炊除唰唰的刷锅声,碗筷的互相碰撞声,案板上的擀面声,菜刀的“笃笃”声,盐罐油瓶的挪动声,开水的咕嘟声,轻轻的咳嗽声...... 多年以来,我一直被这样的声音环绕着,这是在乡村才特有的声音,是过去时光的悠远回声。它是琐碎而踏实的,如同掌在黑夜里油灯跳跃着的火苗儿。更如春雨的绵密无隙,润泽了故乡的每寸土地与每一颗需要抚慰的心灵。它是属于母亲的声音,老屋的声音,爱的声音。它就像一双巨大的翅膀覆盖了整个的我的乡村,我的夜晚。在那一刻,我是依偎在母亲腋下、老屋怀抱里酣眠的幸福的孩子,这种感觉必将伴随我一生一世。 我还想起那雨,那在老屋中痴迷观雨的岁月。每逢农历六至七月,正是雨水最丰沛的时候。此时的雨哪像春雨那般小家子气,淅淅沥沥浅尝辄止的扭捏样子。更不似秋雨的凄清冷漠,无端使人平添愁绪与寂寥。这时的雨是热烈狂放酣畅淋漓的,伴随着一声声的雷鸣,从恍似笊篱的云层瓢泼而下,迷迷茫茫倾在村庄的那些个尖形屋顶,纷纷扬扬自檐头垂落下来,倒像是为一间间冠冕状的房子缀上雨珠串成的旈帘。从窗口望出去,冲刷过房子的雨水汇聚到一起,最终涌出村口,漫上环拱着村庄的河滩、坡地,青了望眼的草便愈见了茂盛与蓬勃。这时的老屋,犹如一条风雨中的行舟,带着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在我看来,我的身体其实就是我的灯笼、我的房子:脊柱为梁,肋为椽;发是苫茅,胸背为墙,眼为窗;气息如炊,心是灯光。我是坐在房屋中央的孩子,我是坐在灯笼里的娃儿,我看到一个广阔美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