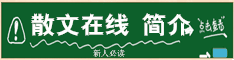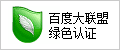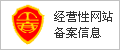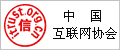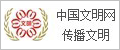散文在线:原创散文发表网!致力于打造中国最专业的原创散文网!
父亲这一辈子

时间:2011-12-02 17:48
散文来源:本站原创
散文作者: 乐山点击:次
|
二000年农历二月二十九这一天,父亲永远的去了。这个憋屈了大半辈子、晚年又被病痛折磨的男人终于得到了解脱,终年78岁。老天实在不公,把他的死又安排在一个不好的日子里。按我们当地的风俗,家里若是“老”了人,必要找阴阳先生看一看日子。若是日子好,则满堂儿孙披麻戴孝,喇叭齐鸣,锣鼓喧天。这是白喜事,跟红喜事一样的热闹。但若是个不好的日子,也就是阴阳先生所说的,犯了什么冲煞,上述的一切都将免去。亲人们不但不能哭,送亡人走时,所有有关亲属还得躲起来,似在躲避什么灾祸。这个规矩古已有之,谁敢不遵?就算你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不信邪怪之类的东西,但家族里还有别的人啊!你敢冒天下之大不讳不管不顾地行事?
父亲死的日子不好,他最后该享受的一点权利也被剥夺了。以前我以为天下都是这般道理,后来发现有些地方并没有这一说。可见,这并非是上天的旨意,而是有人假借上天的名义对一些无辜的亡灵的肆意编派和无端的指控。若那些亡灵地下有知,会不会站出来伸辩和抗争呢?但我知道父亲是不会的。他在人世间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已经使他习惯或者说麻木了。他比谁都清楚,当某种强大的力量迫使你就范的时候,你的抗争就只会像只蚂蚁在呐喊,没有人在乎你在流血还是在流泪。
父亲出生时,家里还有几亩薄地,属勉勉强强过得去日子的人家。但奶奶过世早,父亲上无兄姊下无弟妹,一个人孤苦零丁的,从小就老实本份。虽算不上多聪明,可做事认真,肯用功。由于家境不好,他不能跟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去读长学,只能去读临时性的、简单的识字写字性质的“麦黄学”。从开春读到麦子黄,就是一个学期,也就是一个“麦黄学”。父亲只读了三个麦黄学,就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部头的书。还自学了算盘,用算盘做加减乘除无所不通。在当时普遍缺少文化知识的状况下,人们对文化人的界定是“笔墨算盘是全的”。按这个标准,他也算是个小小的文化人了。
但命运不许他成为一个文化人。解放前,他被拉壮丁在外面当了好几年的兵,由于人太老实,当了好几年的兵还是个兵。临解放时回到家务农,还是过着勉强维持温饱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按说解放后他应该是个翻身农民,该享受新政府的恩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然而命运再一次迫使他偏离了原本的生活轨迹。解放初期,当地有一帮人组织反革命暴乱,因父亲当过兵,就有人想拉他参加。通知父亲时并没说做什么事,只说是到什么地方集中开会。父亲到了那儿发现情况不对,就偷着溜了出来,跑到族上的一个姑姑家里躲了几天。不用说,那帮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收拾了。后来一清查,有人把父亲供了出来。父亲陈述了事情的经过。但证据呢?谁能证明你没参加?姑父一家人站出来作证,但那不算,亲戚作证有窜供的嫌疑。父亲确实什么证据也没有。既然没有证据,你再怎么辩解也是没有用的,指天发誓也不行。就这样,由于承办此案的个别工作人员的粗暴简单,加上父亲的胆小怕事,再加上谁会想得到日后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最后那“曾参加过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竟被莫明其妙地定了案,成了我们一家人的耻辱。
开头几年还相安无事。村里人都比较善良、宽容,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从没人拿这当回事。日常邻里间发生点什么争执,也没有人会想起用这个罪名来揭短,以致我长好大都不知有这回事。
在我小的时候,有段时间见他每天都挟着块算盘,拿着一个账本,到什么地方去上班。每天早出晚归。那段时间爷爷还在世,只是背上长了个疮,整天在痛苦地呻吟。有一天还是中午,父亲就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他跪在爷爷床前号淘大哭,我才知道爷爷已经死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那么哭的样子。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过年时,一村二十几户人家有将近一半人家的对联是拿来叫他写的。每当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的下午,当忙完过年必须准备的东西后,他便把方桌摆好,擦拭干净。再备好笔墨,展纸裁纸,然后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写起来。他写时,找他写对联的人便在旁边给他牵对联。每写完一个字,他便把毛笔在砚里掭一掭,牵对联的人就不失时机地把对联牵动一下。有时他还会抓一把麦麸在旁边,写完一个字,就把麦麸撒上去,少顷将多余的麦麸抖掉,字上便像沾满了金粉银粉似的,真是别具一格,生动而有趣。那时节生活是和谐的,人们对他也是比较尊重的。
后来慢慢起了变化,首先是行动受到了限制,春节期间,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出门。以往春节时都是他带着我一走半个月的亲戚,而现在的亲戚就只有我和弟弟或妹妹去走了。并且出门时,家里还要交待,若别人问起,就说他这几天感觉不舒服。我一直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大人都不说,我也不好多问。直到有一天的一次不经意的发现,才使我了解到整个事情的真相。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队里的仓库边玩耍。仓库旁边有间保管室,门半开着。透过门,我看到靠西边的墙壁上用白纸写着的“我队四类分子名单”。名单上共四人:一个地主分子,两个富农分子,最后一个就是他,名目是暴动分子。当时我的头嗡的一下,浑身发冷。在同伴面前,真感到是无地自容。从上学起,我都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在班上一直是学习委员。不管谁碰到我都说我有能耐有出息,因此我也就自己觉得风光而惬意。突然的这个打击,一下子剥掉了我所有的尊严,以致有段时间不敢面对村里的人。
还是母亲给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我愤愤不平地问父亲,为什么不去申辩?为什么要背这个冤枉?父亲自感无颜,默然以对。我也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原来的工作队早就解散了,你找谁说去?白纸黑字的结论早成了历史。现在莫说没有得劲的帮你说话的人,就是有,人家也得先保住自己,谁不怕死敢去踩地雷啊?幸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段时间的政策还比较宽松,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并未真正上纲上线,成份不好或历史不清的各类人的子女还未受到株连,因而那时的入队、入团、考学也都是一视同仁。我是一九六三年秋季考上的初中。初中设在十多公里外的胡集,是县办的第五中学。整个小学两个班只考取四人,在我们队我是唯一的一个。当小学老师把入学通知书送到家里时,父亲捧着看了半天。我想,这可能是他这辈子里最感骄傲的一件事了。
父亲一辈子都省吃俭用。以前大集体时,在队里劳动分红的钱都交给母亲管理,自己身上从没有什么多余的零化钱。记得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学校组织我们去夏家河的北干渠工地上参观。走到胡家湾渡槽工地时,正遇到我们队里的一群人在那里劳动,父亲也在其中。当时和他们打了招呼就随队伍走了。没想到过了一会,父亲却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把手里握着的几张零票递给我,我说不要,他不由分说地把钱塞到我上衣口袋里转身走掉了。我摸摸口袋,掏出一看,共五毛钱。也许父亲为没有更多一点钱拿出来给我感到了羞愧,而我则是为父亲的艰辛感到了深深的刺痛。
这些年来,蒙乡亲们的格外关照,他倒没受过什么人身攻击。连文革最混乱时期地方两派恶斗,争相将、富、反、坏、右分子弄到街上爬街,也未对他下手。他象一片落在僻静角落里的树叶,已经渐渐被人遗忘了。但政治的阴影却一直笼罩在我们家的头上,并且最终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由于他的原因,我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和弟弟们都不能去当兵,甚至连红卫兵也当不成。说起来我们也是贫下中农,但我们这个贫下中农算是白当了。为此我哭过,也怨恨过他。邻居们都劝我要看开些,他们说历朝历代背负沉冤的人不知有多少,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再哭再埋怨又有啥用?只会给家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活出个人样来,叫别人不敢小瞧了自己。慢慢地,我也想通了,是呀,干嘛要跟自己的家人过不去呢?虽然这事因他而起,但并不是他的错。这些年来他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心中肯定比谁都痛苦。也许正是这种负罪感,使他什么时候都不敢理直壮地责备我们。由此我感到了难过,一种从未有过的同情升上心头。
文革后,戴了几十年的坏分子的帽子终于摘掉了。宣布政策的当天,大队干部叫他写一份体会。当时干部们的头脑里还僵化着,虽然一方面不得已要执行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却又要摆出一副权威面孔,以便在这些昔日的专政对象面前显示一种威慑力量。叫人写体会,无非是要他们承认以前的罪恶,要表示忏悔;现在摘帽是党和人民的宽大为怀,要表示感谢。体会是我帮他写的,摘帽虽不是平反,但总是人生的一个好的转折点。我没有替他去数说以前的什么不是,我只是表示感谢,这感谢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是真诚的。
政治上的枷锁去掉了,按说可以轻轻松松地活上几年。谁知他的腰却像支撑不起上身的重量似的忽地塌拉下来,走路时,上半身前倾得十分厉害。农活是完全不能干了。为了生活,他便到街上菜市场里租了个摊位,卖些从荆门买回的姜、干辣椒之类的调味品。这期间,我们兄弟们都已成家,分开过日子了。他不想麻烦我们,谁也不靠。本来是讲定我们每年要给他们出点生活费的,然而实际上真正能到他们手里的钱却不多。除了我的境况好一点,每年能足数兑现我的承诺外,其他几个弟兄各有各的困难,拿不出钱来。他知道争也没用,便也没有过多争执。只是每天都是早晨一板车拉出去晚上一板车拉进来,顽强地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他们两老。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帮他。帮他的时候,主要在后面推车。因为这样可以让他借助车把的支撑减轻身体前倾的程度,将久不能站直的身体作短暂地拉伸。
我以为生活对他的折磨就到此为止了,然而不是。去世的前几年他又因为前列腺问题导致小便失禁。到街上做生意也不行了,他就和母亲在家里开个小店,卖些糖果、香烟、方便面之类的小商品,赚点生活费。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我们送他到医院看过,也四处为他买相关的药,好像都没什么效果。终于在一次严重便秘的最后一击之下,卧床不起了。尔后是一连三四天的不吃不喝,昏昏入睡,脸上灰白而憔悴,原本是还有点胖的身体也露出了骨形。我们守在旁边,有几次以为他要走了,他却迟迟不肯离去,不知他还在留恋着什么。晚上,母亲一个人守着他的时候,问他还想见什么人,并依次把想到的名字说给他听,他似乎都没什么反应。当问到他是否想见黄蔚时,就见他双眼挂下长长的泪来。这是母亲事后告诉我们的,若我们当时知道如此,说什么也要打电话让她回来。黄蔚是我二女儿,她和她姐姐黄芸两个都在浙江工作。黄芸前不久回来过一次,黄蔚是打算这年春节回来的,两位老人还一直在叨念。在他刚卧床时,母亲问他要不要把她们叫回来,他说不要,没想到这成了他在弥留之际的一份唯一的牵挂。
父亲死后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连遗像都没有。这个卑微了一辈子的人连死都死得这般冷清、孤寂。在他昏迷的时候,母亲已经找人看过日子,并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意思叫他选个好日子上路。而他偏偏选在了这一天走,也许是不愿意经受那个虚假的热闹。他一辈子没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他自己倒不觉得什么,只有觉得愧对家庭,对不起自己的儿女们。其实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以前我们谁都不理解他,怨恨他;后来理解他了,但谁都没和他谈过心,致使他到死都背着这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在他死的时候,没有机会给他开个追悼会,今天我把这些写出来,算是一个弥补吧,愿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2011.9.22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分隔线----------------------------
- 优美散文
-

-
- 借 表
借 表 文/巴木(四川) 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有高中同等学历的都可以参加,而是要先预...
- 小李求职记
小李求职记...
- 痛风之悟
痛风之作 其实,这次痛风的发作是有预兆的。 那几天,只要走路快一些,脚步大一些,右...
- 零食
儿子在一旁用异样的目光瞅着我……是的,他看不懂,更品不出其中的味道,因为这零食已...
- 踏雪瑷珲古城
踏雪瑷珲古城 文/磐石 四月的雪,飞舞在瑷珲古城。端凝与落寞,斑驳了历史的厚重和沧...
- 黄河之滨的村庄
很多年前我还是孩子时,经常听姥姥唠叨她的一些往事,至今难以忘记。 姥姥的老家在黄...
- 本版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