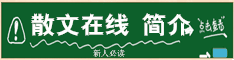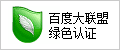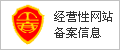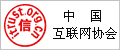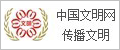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题记:那一年的夏末,在湘西南突然有一种谣言在迅速扩散,似乎在时代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魔鬼在操纵着一切。早已完成了使命的贫农协会又复活了,而且,他们独揽了一切权力。那时的空气里充满了恐怖,混杂着浓烈的血腥味。为了对历史负责,本文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均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但是,为了避免带来没必要的麻烦,文中的人物姓名除了三个被处死的人以外,其余均为虚构的。请读者朋友不要对号入座。
上帝制造的噩梦
邓星汉
公元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父亲要我去水浸坪街上的铁匠铺里找陈铁匠打一百颗铁钉回来。钉子是用来订屋上的椽皮的。农村的木屋,屋顶都是盖瓦的,那瓦片又是架在间隔相等的椽皮上的,而椽皮又是用铁钉钉在屋上的横条上的。那时,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第二年,全国正是武斗的高峰期,城里许多工厂都停止了生产,农村供销社里买不到工厂用机器做的铁钉,父亲就只好要我去找陈铁匠用手工打造。 我的学校就在水浸坪街的前头靠后面一点的地方,旧名叫做朝阳庵,后来就叫成了水浸坪小学。也许是我这个人对学校有特殊的感情,本来是暑假期间,学校里是没有人的,我却要决定先去学校看看后再去铁匠铺子。 当我一走到我的教室门口时,就看到一群人杀气腾腾地从街口子那边冲了过来,前面有几个人把一个用箩索绑成了五花大绑的人像拖猪一样地拖起来,快速地向学校那间小小的办公室走去。我突然见到这样的场面,心里不禁产生一阵颤栗。我既害怕又好奇,就远远地跟上去想看个究竟。 他们冲进了办公室,把那个人重重地摔到地上,他的身体落到地面上时发出了很响的撞击声。那人因为痛,就喊了一声“哎呦!”马上就有人把办公室一侧校长住的房子的锁打开了,那个人又被提小鸡似的提起来,拖进了那间房子里。房门立即“嘭”地一声被栓上了。跟在后面的人有很多没有进去,他们在门外站成两排做看守者。 房间里立即传出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嚎叫:“哎呦—娘啊!”那声音悲惨无比,令人毛骨悚然,像利刀一样穿透了我的心,使我感到惊恐万状。以致我在过后的这五十二年里,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进了房间的几个人中,有三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个名安,他是武冈一所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因为读书读得晚,到初中毕业那年已有二十出头了。他初中毕业时正好文革爆发,他在学校当上了一个造反派小头目。过了一两年后,城里造反的事情少了,他就回乡闹革命,砸瘫了公社党委,改组了大队党支部,篡了他堂兄的位当上了贺东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人称安书记。另一个人名盏,是武冈另一所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文革初期任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副司令。后来也回了乡里,和安一起搞夺权闹革命的活动,他当上了贺东大队的大队长。还有一个人名橙,长得人高马大,高小毕业后就一直在家里当农民。那时候,一个高小毕业生,在农村里已经是算个有文化的人了,再加之他的毛笔字写得比较好,又能说会道,他自己就常以一个怀才不遇者自诩。在他们院子里既横行霸道充头人,有时又还打点“抱不平”,人们对他是既恨又爱,见了他,都要让他三分。安和盏回来造反夺权时,他就抓住机会参与进去,夺权成功后,他当上了贺东大队的秘书。 我听到那个被绑了的人在房子里发出的凄厉的叫声后,就胆颤心惊地退到了那坐教室的外面,竖着耳朵打听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被绑了的人是谁?这时候,街上的人陆陆续续往学校走来,他们在悄悄地交流着打听来的支离破碎的信息。我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了这个被安书记他们抓来的人外号叫东钵子,家就在水浸坪街上。东钵子在解放前好像是个跑江湖的人,不喜欢参加生产劳动。解放后也没改这种习性,经常在外面流窜,背地里做点小生意。因此,他就成了反动分子,经常遭到批判斗争。据说,他在外面参加了地主分子组织的“黑sha团”,前天夜里潜回来了,想要发展组织,报复贫下中农,把大队的干部都杀光。 我在这个学校读书,街上有很多同学,每天都从街上走过,街上的人我是见着面熟的。但是,这个东钵子我却从没有听说过的。刚才我也没有看到他的脸,事实上到东钵子死了后,我也是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至于那“黑sha团”我就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听着人们的议论,我觉得是一头雾水,只是从每个人的脸色和神情中,我感到了一种使人心惊胆颤的恐怖从四面八方滚压过来。 那间房子里再也没有发出叫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东钵子一被推进去后,就遭受上了一种叫做“踩绷子”的刑法,他一下子就痛得昏死过去了。 过了一会,又来了一队民兵。安书记出来了,他吩咐在外面站岗的那些人和刚来的民兵把围观的人赶走,然后安排他们到学校周围去站岗放哨,要求他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不准放任何人进来。这样,我的可爱的学校一下子就成了个阴风凛凛,森严壁垒的地方了。 我不用他们赶,抬腿就往街上的铁匠铺走去,我知道我的使命是要赶快找到陈铁匠把铁钉打好。 到了陈铁匠的铺子里,只见他忙得大汗淋漓,带领徒弟甩开膀子在打造梭镖。我见过连环画上工农红军手里拿着的梭镖,感觉陈铁匠打的刀和梭镖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陈铁匠还不会打梭镖,为了赶任务,就自己创造性地从sha猪刀演变过来一种比sha猪刀小一点的刀型,因像条小鲤鱼,陈铁匠自己把它命名为“鲤鱼刀”。但人们还是习惯性的称之为梭镖。只听得拉满把的风箱发出“噗、噗”的喘息声,炉子里闪动着鲜红的火苗。待铁块烧到火候时,陈铁匠右手拿铁钳夹紧铁块放到铁砧上不断地翻动着受力面,左手抡起锤子敲打着铁块。他的锤子落在哪里,徒弟的甩锤就砸向哪里。两师徒的手臂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弧线,身体一俯一仰,有节奏地和着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给人一种力量的惊憾。地上已经有了好几十把铮亮的梭镖了,看来,他们今天一大早就一直在干这样一件事情。我心里感到好奇怪,谁要打这么多的刀干什么用呢? 我在陈铁匠的身边站了好一阵了,嘴里不停地对着他喊:“陈师傅,我要打钉椽皮的铁钉!”他是认识我的,但这会儿他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仿佛我不存在似的。好不容易等到他把一把新刀子打好后直起腰来,我才抓住机会把要他打造铁钉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听了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对我说:“不行啊!这几天都没有时间啊。这是大队安书记交代的任务啊!”我还是苦苦求他帮忙,说家里等着急用。大概他是认识我父亲的,他就婉转地对我说:“你回去吧,告诉你爸爸,真是对不起他了。你三天后再来取吧,我一定打好。”我见他说得诚恳,又看看他那忙碌的场面,知道今天是没有希望的了,就只好怏怏不乐地往家里走去。 回到家里后,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父亲。因为没有铁钉,父亲早从屋上下来了,改做填土的事情。我感觉他好像已经知道了抓东钵子的事情了,他对我说的话一点也没有感到惊诧,只是淡然地对我说:“没打成那就算了,过几天再去吧。”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像往常一样,端着饭碗到爷爷的堂屋门槛和条石上分散坐着,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大伯就很认真地对大家说:“现在,有一些不死心的地主组织起黑sha团,专门杀害党员干部和土改分了他们的田地房屋的贫农。消息是从道县传来的,据说道县的黑sha团凶残得很,一夜杀了几十个大队干部。道县的干部就迅速组织起贫农协会,抓到黑sha团的人就把他们杀掉。黑sha团暗地里到处串联发展队伍,组织很严密,有司令、参谋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交通员等。前天,新宁县的贫农协会派人来报信,他们那里的黑sha团成员招供了,说我们这里也有人参加了黑sha团,街上的东钵子就是黑sha团的团长。今天,贺东大队的贫农协会已经把东钵子抓起来了,正在审问。我们大队暂时还没有听说有参加了黑sha团的人,但要提高警惕。我们大队也成立了贫农协会和民兵护卫队。从今晚开始,大家睡觉要警醒一点,过去那些防身的家伙要放枕头边,一有情况,大家就要马上起来。”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划入到贺东大队来,我们的行政区划是黄菜大队第一生产队。大伯是生产队长,三叔是大队民兵营长,他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大概大伯和三叔他们是早参加了大队的党员干部会的了,情况都知道了。三叔是很少到这里来吃饭的,今天中午他也来了。他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枪法特别准,曾代表中国军队参加了世界军人射击比赛。三叔就接着大伯的话说:“大家不要怕,如果有黑sha团的人来我们这里,你们只要跟着我,听我指挥就是了,但千万不要到我前面去,我的鸟铳是散弹的,到我前面就怕误伤呢。”爷爷年轻时就备了两把鸟铳,现在,一把是三叔在使用,另一把是四叔在使用。接着,三叔又通知我的两个堂哥被选进了民兵护卫队,明天去大队部领取梭镖,每天晚上都要去参加站岗和巡逻。我们家里是有习武风尚的,听了大伯和三叔的话后,大家都表态要立即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家族,准备和黑sha团做斗争。吃了中饭后,爷爷就从楼上把“齐眉棍”拿下来了,四叔就把鸟铳的火药袋装满了火药和铁砂,大爷爷就把腰刀磨锋利了放在枕头底下。一下子整个家族就进入了一种临战状态,枕戈待旦。 从此,人们每天都在关注着有关黑sha团的消息。 第二天上午,我就听说东钵子已经供出了他的下线,说贺东大队的另外两个地主瑞和柏也参加了黑sha团,地主瑞是连长,地主柏是通讯员。这实际上是东钵子在受不了刑罚时胡乱编出来的。安书记就马上安排民兵把这两个地主抓起来严刑拷问,要他们交代出同伙来。 这两个地主实际上就是在解放前比一般人多吃了几口饱饭而已的农民,都是没文化也没有什么见识的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从何交代起,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去编故事乱咬别人。不管怎样用刑,从他们的嘴里都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口供。他们痛得受不了了,就说:“我交代,我交代啊!”把他们松了刑具后,又说:“我真的是冤枉啊,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东钵子一直是走江湖的,他胡乱一顿编造,却和安书记他们得到的有关黑sha团的消息大致相同。他为了不再受刑法,又还丧心病狂地把本大队的地主柏和地主瑞还有伞江大队和他认识的两个地主都扯进去了,说是他发展的成员,他们是深夜里在蔡家亭子开了会,布置了任务。这样,东钵子算是坦白交代了,安书记们也就没对他再用刑了。只有地主柏和地主瑞这一天下来,连过三堂,受用了“踩绷子”、“夹筷子”、“吊半边猪”这三种刑法,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那时候,消息传播速度非常快。到了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有人传来消息,说地主柏跳入街背后的大阴潭自杀了。到了晚上,我就听说了有关地主柏跳潭自杀的详细情况。原来,地主柏从给他送饭的儿子说的话里听出了此命不保的意思来了,心里十分惶恐,他不知道贫农协会的人会用什么方法处死他,他想起阎王爷的四十八种刑法,不知这些人是把他刀剐还是活埋?是把他绞死还是下油锅?他在心里五花八门地想着,身体打着哆嗦,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他想,如其被活活折磨死,还不如自己找个痛快点的死法。于是,他就横下一条心,今天就跳入大阴潭淹死好了。 决心定了以后,地主柏就故意大声地对着看守他的人喊:“我要拉肚子了。快放我去上茅厕。”两个看守只好把门打开,让地主柏去上厕所。地主柏是被反剪着双手绑住的,两个看守跟在后头看管着他。地主柏一出门就撒腿向前跑去。两个看守以为他是憋急了,开始并不在意,只是也跟着小跑起来。谁知地主柏到了学校的厕所门口并没有进去,突然拼命向厕所背后的大阴潭跑去。也是横了心了,力气也突然大了几倍似的,他被紧紧地绑着手臂,却还跑得像风一样的快。这时候两个看守才反应过来,知道地主柏是想去跳潭了,也就立即加快脚步奔跑着去追赶地主柏。他们边追边喊:“你跑哪里去?快停下来!”可是,为时已晚了,地主柏已经快到阴潭边上了。最后,就在看守伸手将要抓住绑在他身上的绳索时的那一刹那间,地主柏倒地一滚落入了大阴潭中,让背后的看守抓了个空。阴潭边离水面有十几丈高,地主柏落入水中时发出一声巨响,溅起一串几米高的水花。地主柏没能挣扎就垂直向潭底沉下去了,阴潭宽阔的水面立即又恢复了原来那死一样的平静。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县公安局来了两个干警,说要找安书记们传达县委县公安局的指示:贫农协会不能私设刑堂,如果这些人真在组织黑sha团,那也要把他们交给公安局来调查处理。但是,这两个公安干警遭到了站岗的民兵的严厉拒绝和街上的贫农们的围攻,不准他们向安书记所在的小学校靠近一步。这两个干警也就无可奈何地回县城里去了。 站岗的民兵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安书记。安书记觉得必须马上处置东钵子和地主瑞这两个人了,不然,公安局还会来进一步干涉这个事的,到那时候他们就没有权利处置这些人了,贫下中农就解不了心头之恨了。而且,再拖下去还可能会节外生枝,再发生类似地主柏自杀这样的事件。于是,安书记们就连夜召开会议,讨论怎么处置这三个人。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三个人秘密sha掉。但怎么sha呢?由谁下手sha呢?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用梭镖sha,由安书记、大队长盏、秘书橙和贫农协会春生主席各联络一个人作为先锋手出第一刀和第二刀。为了能坚决完成这件事情,他们从民兵和贫农协会里挑选了五十个坚定分子组成行刑队,也为了替那几个先下手的人保密,决定五十个人每人至少要上去sha一刀,这样,都沾了血就没有人敢泄密了。刑场就选在街背后田垄中的小阴潭边那块草地里。 第二天,安书记们就分头秘密去通知那五十个坚定分子开会,又从这五十个人中做通了四个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担任最先下刀的先锋手。这四个人的名字是严格保密的,不对任何人宣布,只有他们四个人知道自己的任务。 公安局的人到来和地主柏的自杀直接加快了东钵子和地主瑞的死亡进程。 安书记们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九点行刑。晚上把五十个坚定分子召集在一个叫杨家坪的山包上秘密开会,由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虎跛子讲了致死的要害处并做了动作示范。然后,对行刑的过程做了周密安排,严申了纪律,要求下手时要又狠又准,每个人至少要出一刀,永世不得泄露这五十个人的名字。为了不让一般群众知道行刑的是那些人,规定大家要在第二天天亮之前趁黑到达学校里集合。刑场周围进行清场,各个路口都派岗哨把守,任何人都不得靠近。最后,春生主席把一只公鸡提在手里向空中划了一个圈,对着大家严肃地说:“苍天在上,大家看着,有不出刀的,泄露秘密的都和这只鸡一样!”然后,他一刀就将鸡头砍下,把鸡血滴在一个盛满烧酒的脸盆里,再把酒分在每个人拿着的碗里,最后喊一声“喝!”大家就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了。然后,就各自回家里磨刀做准备去了。 安书记们也学着古人的规矩,派人暗中通知了东钵子和地主瑞的家属,要他们明天早上送“上路饭”来。据说东钵子的儿子为了减少他受刑的痛苦,就想方设法故意把东钵子灌醉。他儿子炖了一只鸡,温了五斤“二锅水酒”,送来陪着东钵子吃,不断地劝酒,东钵子说不喝了,他儿子就说:“酒好呢,难得喝到,再喝一杯。”一直到东钵子醉得不醒人事了才罢休。地主瑞的儿子就没有这样的孝心了,就是给他送了一碗饭,上面盖了一些豆角做菜。地主瑞知道死到临头了,恐惧和悲伤使他难以招架,看着这样的饭菜哪里能吃得下呢。他泪流满面,根本就没有动筷子。 九点整,那五十个坚定分子,个个手持雪亮的梭标(实际是陈铁匠打的鲤鱼刀),雄赳赳地走了过来,只见安书记振臂一呼:“把犯人押赴刑场!”,这些人就把东钵子和地主瑞绑起来,像提小鸡似地提起来快速向小阴潭走去。东钵子已经醉成了一滩烂泥,实际上就是被拉死猪一样的拉着向前冲。而地主瑞却吓得浑身打着哆嗦,脸上黒汗一股一股地往下流。 我吃了早饭,就听了父亲的吩咐去街上的陈铁匠铺子里取铁钉。当我走到石脚院子时,就听到有人在大声地说:“今天sha东钵子啊!今天sha东钵子!”我一听,就觉得好新奇,也感到很胆寒,心里却又忍不住想去看看把戏,便就飞跑起来。等我一口气跑到新屋刘家时,老远老远就看到一队人马向小阴潭这边冲过来,我猜想那就是sha东钵子的队伍吧?我就猫着腰从一块大石头后面绕过了在路口站岗哨的民兵的视线,快速跑过去趴在小阴潭边上一块高高的岩石上观看,心里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由于这些人的注意力根本就不放在警戒上,而是集中在行刑的过程中,我在那里偷看也就没有人发现我。 那一队人马把东钵子和地主瑞拖到小阴潭边的草坪上,就把他俩从不同方向往草地上一丢,就有虎跛子和另一个叫旱的壮年人各冲向地主瑞和东钵子的身前,举起梭镖就猛力刺下去。 地主瑞本是脸朝下扑向地面的,可是他痛得难受挣扎着又把脸翻过来了,眼睛直瞪着虎跛子,把个虎跛子吓得心里愣了一下。虎跛子赶忙把地主瑞一脚踢翻过去,然后再将梭镖向地主瑞的脖子上刺过去。可是,由于有刚才的那一愣,他的手发了软,本来是要刺向动脉血管的,刺出去的梭镖却改变了方向,最终刺向了地主瑞的喉管,痛得他大声喊叫,在地上打着滾。紧接着就上去了年轻人丘,丘见虎跛子这样上过战场的人都失手了,他的心里也着了慌,虽然是按照昨晚制定的方案刺向了地主瑞的胸口,但也是偏了方向,不中要害。地主瑞痛得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用牙齿啃着泥土。这时,后面的人蜂涌而上,各人乱刺一刀就走。有的刺在胸口上,有的刺在腿上,有的刺在手臂上。到了后来,不知是哪一个人无意地刺中了地主瑞的动脉血管,血喷射出来,这时的地主瑞也是痛得不能动弹了,不一会儿,地主瑞就绝了气。后来,地主瑞的儿子来收尸时数了在他的身上有三十六个刀口。地主瑞是被乱刀杀戳,活活痛死的。 东钵子因为醉得如死猪一样了,躺在那里任人屠宰,不哼、不喊,也不动。旱照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梭镖,然后,还转了一圈才抽出来。跟在后面的甜,年轻力猛,也照着东钵子的胸口再填了一刀,他的力气真猛,刀都把胸膛刺穿了,碰到了地下的石头,刀尖都卷起来了。东钵子基本上就是这两下子要了命的。后面跟上去的人,虽然出了刀,但都是完任务式的了。有几个人走近去见东钵子早已死了,梭镖举都没举起来,只在东钵子的衣服上点了一下就走了。 完成了任务的人把梭镖往草皮上摖干净了血,就各自回去了。整个过程用时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最后,安书记,春生主席、盏、橙等把东钵子和地主瑞的血衣剥下來,和同捆绑的箩索浇上汽油一把火给烧掉了。然后,他们一起回学校去了。 待五十个坚定分子走得差不多时,我也就离开了小阴潭向街上的铁匠铺走去。 安书记们原来以为他们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严密,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施展残暴的这一幕。可是,当场就被摄入了一个十岁儿童的明亮的眼瞳里,成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背脊骨就发冷。那时,我可真是懵懂无知,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当我走到学校后面时,我看到有四个县公安局的人在那里向小阴潭方向望了望,那里有一缕青烟在轻轻地飘动,然后,他们中间有人感慨地说:“还是来晚了一步啊!”说完,他们就赶向散江大队去制止这种事件去了。 伞江大队也照着东钵子的口供把那两个参加了黑sha团的地主抓起来了,同样准备在这一天都杀掉。但因没有人敢第一个下手而迟迟未决,结果被公安局的人赶到制止了,把那两个地主当场放了。后来,人们都感叹那两个地主真是运气好啊! 我来到陈铁匠铺子里的时候,见陈铁匠已经不再打那种自创的鲤鱼刀了,他在开始给我打钉子了。他对我说:“小孩子,你再等一个小时左右吧,我正在抓紧时间给你打呢。”我说:“好的。辛苦师傅了。” 这时候,那个勇猛的甜提着他刚才杀卷了的梭镖进来了,他招呼也不打就把梭镖放在陈铁匠的磨石上磨起来,只见那磨石上的水中有鲜红的血丝丝流出来。陈铁匠放下手中的铁锤,冲过去一把夺下甜手中的梭镖猛地往铺子外面丢去,嘴里大声骂:“莫把邪气带这里来呢!”甜也不敢再说什么,走过去捡起自己的梭镖就走了。 甜是盏的亲弟弟,当盏做他的工作当先锋手时,他提出的条件是让盏把从造反派组织里借回来的自行车给他骑三天。他特别羡慕盏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摇头摆尾、得意洋洋的样子。 其实,做通另外三个先锋手的工作都很容易。旱和春生主席是一个生产队的,春生主席答应把生产队长给他当。丘是孤儿,两兄弟都没有娶到老婆,橙就答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虎跛子是共产党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立功。安书记就对他威逼利诱,说:“你是老革命、老功臣了,与阶级敌人斗争要起带头作用。当然,我知道你家庭困难,就给你免去十年的党费吧。”虎跛子就乐意地答应了。 陈铁匠是受过师傅告诫的,这刀子可不能打造得太多,因为刀子都是用去杀生的,所以,刀子打多了是有罪过的。这一阵子,他日日夜夜加班加点打成的刀子有千多把了,而且,刚刚看到自己打的刀子被用去杀了人,一种内疚和负罪感使得陈铁匠感到惶恐不安,心里十分烦躁。恰好,又有一个老人进来求他打把杀猪刀。陈铁匠气不打一处出,铁青着脸,对着那个老人没好气地说:“不打!”老人又问陈铁匠:“为什么不打呢?难道我给不起钱?”陈铁匠气急败坏地说:“不打就是不打!你不知道去合作社买?!”老人就知趣地往外面走,边走边在嘴里嘟咙着:“去买就去买。知道打铁又有什么了不起!” 接下来,紧张的空气并没有因为sha了东钵子和地主瑞而缓和,仍然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到傍晚,就有人向民兵护卫队报告在某座山上发现有烟火,是不是黑sha团的人在煮饭吃啊?护卫队的领导就一边派人去联络周围大队的民兵一起来“搜山”,一边马上带着民兵赶去把山脚围起来,不使黑sha团的人跑了。结果,忙乎一个晚上,人挨着人把山像篦虱子一样的从山脚到山顶篦了一遍,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如此这般反复搞了几次后,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人们就不太相信这类事了。再过了一段时间,风声就慢慢地消失了,生活也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只是人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偶尔谈起黑sha团来,话题大都是为这股阴风的起因而感到疑惑不解。 有人说:“古有成语:七死八活,乱七八糟。今年逢七,就是个乱世之年。东钵子这些人,是天要收他们了,不生股这样的怪风哪来要他们死的理由呢?”这似乎就是当时公认的解释。 死的就这样冤枉地死去了,sha人的依然逍遥自在地活着。五十多年过去了,昭雪无据,问罪无凭。真如人们所做的结论一样:这是上帝给那些人制造的一个噩梦! 然而,这噩梦真的是上帝制造的吗?
后记:时代的潮流,浩浩汤汤,顺者昌,逆者亡。失势的阶级要顺应历史,逝水怎复?得势的阶级要施仁政,建法制,关注民生,岂可再扩大阶级仇恨!相逢一笑泯恩仇,青山依旧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闲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