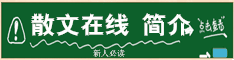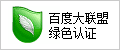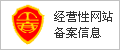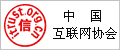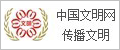|
一、拐子茶馆 拐子茶馆的主人是我家沾亲带故的挂角亲。我们山上的一个姑娘填房嫁到了街上,因为是地邻与父亲姐弟相称,我叫他大孃。大孃命短,早几年已经死了,剩下姑爷和一个老表,老表喉包气喘是痨病秧子。靠自家场口的房子搭了个偏偏棚子开了茶馆在竹林头。老表勤快,把竹林里竹叶、笋壳、鸡屎,打扫得干干净净。竹竿橫枝穿叶,在梢顶弯成一个穹,不见天日。夏天麦蚊子多,竹林上时常挂着陈艾青蒿来驱蚊,麦蚊子太凶的时候姑爷就用稻草烧烟来薰,这是应急一时。后来天柱村的房匠子骆宇林挖来一窝夜来香栽在竹林碥上,麦蚊子苍蝇都少了许多。 因离家太远,在小镇读书中午就在姑爷家搭火。放学吃了饭,时间还早,我就帮老表收拾茶桌。喝白了的茶倒在筲箕里,收集起来的干茶叶子,用来装枕头很好,还酽沉的茶便倒进一个大茶壶,当凉茶留给到茶馆里讨水喝的人解渴。茶碗和茶碟放在水盆里,要用丝瓜布擦净茶秽,在清水里漂一漂,放到筲箕里凉干再置放在茶柜上的茶盘里。待有客人来时,茶柜上二十个茶碗配好茶碟,像一朵朵栀子花开在老黄的柜板上,二根指拇拈一撮花茶放在白瓷茶碗中,再一一盖上茶盖。有人来,及时取用。平素茶具都用洗得干净的白纱布遮盖着。完了,去压水井把储水的石缸压满水,歇下就差不多到上课时间了。 姑爷腿不方便,常守在茶馆门口的副食品摊上,进来了客人他便招呼。茶馆的堂中只有几张桌子,大场是在过堂后门的竹林里。炊炉的灶台在后门的干檐上,清早开火的时候,就闻到一股生铁味的煤烟气,这种味道是不是煤炭燃亮的成份使然,有利剑的雪冷铁腥味,让人想起烽火的战争。那烟起初是黄色,渐白色,后就青色了。煤炭不比山柴火那么熊,火信子透明的热能却比柴火来得刚烈。煤上面架了钢板,钢板上有一个一个与壶大小相等的洞,炊壶就架在上面煮。钢板后方凸起一块泥台接着烟囱,可以听到那风火穿过烟道在房上洒下细微的煤灰,瓦房积了黑雪一般厚,下雨的时候流下的天花水都是黑汤。檐口的吊檐上挂着一窝虎头兰,叶子长而垂,跳起来可以摸到他的叶子,夏天开些蓝色的花,兰草的根部没有土,被成长的巴岩姜包着,平常也没有人浇它,一样活的很茂盛。 姑爷的副食摊分为二部分,一部分卖糕点饼子水果糖,针头麻线,女活一类的东西。另一部分卖的是“军火”,打枪子用的火药,炸药,铁砂子,还有装沙子的葫芦。姑爷平常不善言笑,这是否缘于他的不幸才作强,街上的人都觉得他的城府深。 但这并不妨碍茶馆的生意。茶馆的侧边是屠宰房,猪下水和猪毛的气味,有时透过篱笆传过来,茶客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好。这气味常勾起他们打牙祭吃肉的感觉,肉瘾发登了,几个人就逗钱打平伙,隔壁喊一声,新鲜肉就甩过来一坨,就在茶馆加工,比进馆子头强的多。 茶馆的生意一般都是靠老茶客撑起。老茶客不单单是来照顾生意,还会扯朋式,讲农纲,吹壳子,逗人笑。真正闷起喝茶也不过一道水二道茶三道四道就漂白了,要一天半暇的寡坐也难。如果有三二个日白客,扯谎聊天,吹起牛壳子,场子就圆了。朋友的朋友相好就图个闹热,这光阴就好混。人气就是生意。乖孙乖女到茶馆来找老爷,大爷幺爸也得给三分钱买块冰桔糕打发了早些回去。山乡捎店子茶铺子,一脉相承。 打枪子的撵山狗拴在竹林边的木槿花桩上,在隔壁屠宰场要了一碗猪残废血喂了,嘴筒窜在胯夹卷了尾巴歇气,蚊子飞过,它苍耳子便摇摇。砂枪和枪颠上的野兔斑鸠、取下来挂在竹枝上,卖野味的馆子来买,落得元把二元钱在中山服的上衣口袋里,要茶都是五分一碗的清溪茶。 冬天过去,春天的时候,茶馆来了一个瞎子算命匠。瞎子的命算得准,给茶馆带来了繁荣。这引起了派出所的注意,治安人员来捡了瞎子的摊子,信命的人更是千方百计来找瞎子,瞎子免开金口命价高涨,想改变命运的人拼命求方子。瞎子不敢露面,姑爷就给他腾了一间屋子,整日坐在黑屋子里。算命的人要先在姑爷那里挂号,约好了时间挨轮子算命。姑爷每三五天就拿挂号的竹片子给瞎子的竹牌对帐分钱。没人的时候瞎子也出来喝茶闲谈。派出所再找算命匠,瞎子依残卖残,渐也习以为常。 星期二的下午不读书,太阳又大,我就帮老表卖茶。几个茶客已靠在竹子上架着二郎腿。啄瞌打睡。刘烧房的“待诏”,待诏不是官名是农村上的剃头匠。挑着一头热一头冷的担子吆喝进来: “有人剃老壳没的?” 房子匠骆宇林随后进来说: “剃块光头好多钱?” “一角。” “待诏”和老表点头,一分钱要了一盆热水,把玻璃镜子挂在篱桩上,摆好翻板椅。骆宇林坐上去围上白市布围单。把头伸进水盆,“待诏”捞起已泡胀的皂角在骆宇林的头上使劲搓。 “待诏”转头对我说: “小鬼,考你一副对子?就是我们剃老壳的。” 赵中发接过话头问:“啥子呢?” “理发理发有礼有法。考你也对不上!” “修行修行不修不行。” “吔。看不出来你赵中发,板眼硬是深呢。” “咋弄发,找到赵中发就有法。”骆宇林道。。 “牛圈头伸出马嘴来了。”赵中发顶了骆宇林一句。 “尽都城楼上点灯——高明。现在就骆宇林剃光头出副对联……” 大家看光筋干棍的骆宇林,剃光的头像拨郎鼓。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头拄着拐棍走进来,听见姑爷喊: “青狗,给常青大老爷泡杯好茶。” 常青大老爷是解放前的伪乡长,成都锦江书院的肄业生,大家表面上视他为老朽,骨子里是敬着的,不比袍哥舵把子起家,历来信奉礼义,懦雅风度。赵中发捏了把鼻子正要往桌子上抹,慌张中忙把鼻涕抹在自家的长衫上。 “待诏,你又在麻广广了。是不是这副对联:‘十指拎骷髅,一刀斩葫芦’?” “老太爷说得是,我癞蛤蟆翻筋斗,显屁儿白了。” 常青大老爷,手里提着胶线编过的玻璃茶杯,老表接过去拈茶渗水。老人随手给了一角钱,老表找零。 “不找了,下回又来。”他向各位再会,拄着拐棍念了一句: “相逢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 大家看他的背影转过了老墙,似乎松了口气。 待诏叫我拿笔记下来,小纸条折成小方块收藏在烟袋里。 赵中发从萎靡中回过神来了兴趣,正要发话。见一妇人虎汹汹地进来,走到正在掏耳朵的骆宇林面前,婆娘扯起嗓子就骂开了: “骆宇林。龟儿子。” 骆宇林一挣,拍巴巴掌说: “你会骂。” 婆娘又骂:“骆宇林,狗杂种,少娘老子教的,整人也不是你这种整法,哑善狗咬人不开腔。” 骆宇林站起来,又坐下说: “骂的高,风吹过;骂的矮水打过;不高不矮自己受。” 婆娘泼辣,抓起骆宇林的衣领要扇他的耳光,骆宇林一把将他摁在椅子上。说:“你骂,落雨淋龟儿子,落雨淋的不是我,是狗杂种。”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恍然大悟。 岳家是有名的吝啬鬼,对人很苛刻,房子匠骆宇林就日他的怪,新房盖好的当天晚上,天下起了瓢倒的大雨。整个房子都不漏,偏偏俩口子的床枕头上漏雨,弄的两口子一夜未睡。第二天,在街上找到坐在茶铺子的骆宇林。 房子匠骆宇林是茶馆中较年轻的一位。他走村串户,帮人翻修房子,只要每天向队上按一角五分钱的劳动日上缴给生产队,一年就是全勤的出工〔按:集体化时0.15元/10个分值〕,所以他有许多的闲余,成了茶馆的常客。因为骆宇林的故事多,有人说他得了鲁班的真传,会施道法。 岳家婆娘斗不过房子匠,留下恶毒的咒语走了。 俩人斗嘴的时间,门口进来了茶客,河生大伯和根山老爷。 “青狗,来人了倒两碗茶,要鲜开水。” 青狗老表应道:“晓得了,两位请座。” 我把茶碗跟两位摆好,青狗老表提了铜壶来渗茶,高吊落水,茉莉花在杯中翻波涌浪。 “茶钱这儿给了。”几只手伸到青狗的面前。 “谢了,都谢了。” 青狗收了瞎子的钱:“算命先生给了。” 不知道瞎子是咋认钱的,我便凑上前去,只见他摸着一叠钱,抽出来的是二分纸币,很准确。我问:“先生,你摸得到钱的大小么?” “瞎子见钱眼开,和尚见钱牵口袋,钱啊,那个都认得到。”河生说。 “滚球你的。就你牛吃笋子屙背篼,会编。” 赵中发从茅房出来,拍了青山一把,“老伙计,没给上,下回。” “咋回回都你给呢,茶在水中飘,飘在哪方算哪方。” 我就抱着书在茶桌上读。茶客们谈天说地,他们偶尔考考我一些生僻字,比如说:屠夫,他们叫刀儿匠,而不用“刀儿匠”要用“deng儿”,赵中发说:“小”字下面一个“大”,是不是读“尖”,我答“对呀”。“大”字下面一个“小”呢就叫“deng儿”(陀螺)。又说:蹲下来,四川话的“ku”怎么写,我说:“蹬下”也可以,他说:只说“ku”,“立”字上面去掉一点就叫“ku”,你在草丛里“ku”下去就见不到头了。还说:“虫”字下面一个火叫什么字?叫“niu”,火烧虫你说它“niu”不“niu”。又问“肏”是什字?问的时侯他们都阴笑,暗里揶揄我的无知,显示他们聪明。 我在门上写一个“活”,问他们什么字?他们说:“活”。 错!叫“阔” ?! 又在竹子下面放作业一本,读啥呢? ……? 再加一个蛋,叫啥? 笨——蛋! 常青老太爷说∶“过来,你娃精灵。出副对联你来对,对上了,我打一斤烧酒招待在坐的;对不上你娃就去捡狗屎卖,逗钱买烧酒!” “说,我们等烧酒喝。” “竹篮装笋子,母怀胎。下句……?” 看着等我笑耍儿的茶客,搔首想:竹篮老母竹,笋为竹子,即母怀儿胎。……? 老茶客烟杆撬起,吞云吐雾,一脸怪笑。老太爷呷口茶,在口里鼓漱了半天才咽下,慢条斯理架上二郎腿,右手食指鸡啄米,在桌上突突有声,敲击我的脑壳。不敢看他们的脸色,抬头看场外的谷田,稻谷已散子,一下想到:谷草拴秧苗……竹篮装笋子。拍手叫绝! “谷草拴秧苗,父缠子” 在坐不出声,老太爷喊: “掌柜的,打一斤酒来。” 打枪子赵中发倡议道:“好久没这么齐过了,今天大家打一屯平伙,如何?青狗,拿去,把野麻兔剐了烧青豆米,算一份!” 瞎子响应:“铺到几条命不算,一份炒猪肝。” 林待诏说:“铺到几个脑壳不算,一笼下水烧苦瓜。” …… 我要背课文,给青狗老表说一声,拿了书穿过竹林,来到莲花塘。六月的莲花开得正繁,一排柳树在沟边上挡着了那边的稻田,只听见稻田那边传来蓐秧草的水响,偶尔一坨水碾板草草甩到沟边上发出“叭”的响声,吓得过路人双脚一跳。我坐在石桥上,把脚伸进水里打水弹花默背着课文。课文里的文字象秧苗生长在心田,被风拂来拂去的动荡,总有稻螟虫在上面乱飞,于是忙闭上眼睛,文字才没有乱飞,在脑海里栩栩如生,捡点文字,倒背如流。 远望着白平观山上,校长带领学生用石灰粉写的:农业学大寨。自己的家就要走过字底下。那字近看像是下了霜的草坪,一个字就是一幢房子的宅基般大,远在新津的永兴场,都能看见。就像陈永贵坐在中央的交椅上,万众瞩目。山上层层的梯田,种着桔子和山梨。果木的浓荫里是枞树搭的尖茅房,房顶扎着草髻,象高古的道人隐居在林壑。山中一时传来铁砂枪的枪响,一朵白烟从林中窜出来,接着听见撵山狗的嚎叫声。是赵中发他们上山围捕山鸡了。山鸡似乎没有一枪命中,在狗的狂叫声里接连发出“铳、铳、铳”的枪响,田间地头的庄稼人,把头伸出来瞭望。望着看着天色就开始卖麻布了,远山退缩成一抹黑影。队长一声哨响,收工了,零落的田野开始寂寞起来。 二、山色故作云姿态 青狗老表的病一直不见好,脸色泛青,喉咳气喘。姑爷给茶客闲谈的时候,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大家从宽处安慰他,尽力想撮合青狗的婚事。青狗已经二十四岁了,也没见过人给他提亲,这让姑爷很着急。 星期一中午,我放学在教室里打扫卫生。姑爷柱着拐棍来到学校找我,说是青狗“看人”,叫我快点回去帮忙。我便背了书包,也不等他先跑回了茶房。刚转过丫字口,就见门口围了一堆人,我挤进去,见瞎子正和一个老娘子说话,侧边坐了一位清秀的姑娘,不见青狗,我去房间放下了书包径直去堂屋找他,青狗却躲在门后,从门缝偷看那女子。我捶他一拳:“去嘛,出去。” 我和青狗走出来,姑爷提了一刀肉也回来了,还有鲤鱼。进门就喊:“赵中发,帮下忙。” 在竹林喝茶的赵中发和骆宇林都过来了。 接了姑爷手里的菜,姑爷便吩咐煮午饭。 姑爷走到竹林吆喝到:“在坐的,今天晌午请大家喝烧酒,都不要走了。” 众人高兴,都过来打帮手,烧火弄饭。 姑娘不怯生,眼神平静,粉红的的确良衬衣,腰身窄小,两条长辫垂到了腰际,米色的裤子直一线,脚上穿着一双白凉鞋,足和手没有下过田,白净细嫩。她眼里似乎在寻找什么,终不得见,于是游离起来。 青狗虽是站在门外,一点也不打眼。姑爷走过来在身边耳语了一阵,青狗去了里屋。那女子的眼神追随着他,在门上停留了一刻。姑爷抓来馃子和糖,放到姑娘的面前,茶客和居民交头结耳悄悄低语。姑爷高兴的招呼大家:“里面坐。” 又叫我给大家泡了茶,那竹林里也就都坐满了人。 青狗换了白衬衣出来,姑爷又把手表抹给他戴上,老表清瘦,样子文静。穿了皮鞋卷边裤添了几分气派,有点像电影里的文弱学生。特别是他的不苟言笑,使他稳重了几分。 他坐到姑娘的对面,往茶杯里渗了水,“喝水。” 姑娘点头。 同桌的老娘子是媒人,便说了一些姑娘的情况:姑娘没有做过农活。高中毕业了一年,本来是在村上代课的,被人挤下来了。姑娘太秀气,干不得体力活,想找街上的居民。想起树青合适,想撮合这一门亲事。 树青是老表的大名,这媒婆也常到茶馆来,对姑爷家的情况一清二楚。 “树青你表个态,中意呢,就算我做到了人情;不中意呢,就谢了你这杯茶。” 树青没动,只是看姑娘的眼神。 “琼芳,你表个态。”媒人说。 “我回去给父母说一声。” “子女征求父母的意见是对的,你们有话可以自己去摆谈。”媒人说完,起身准备走人。 姑爷一定要留二人吃饭。在坐的跟着帮腔: “事情成不成,饭是要吃的。” “饭菜马上就上桌了,忙也不在这点时间上。” 赵中发把他打的两只斑鸠烧了端上桌,又说:“树青拿酒来噻,你娃福气来了,还不快点谢媒人。” 说得媒人眉开眼笑:“我只是穿针引线。” 饭菜上了桌,姑爷招呼大家吃饭,众人都道谢走了。只有几个老茶客,围拢来喝酒。 骆宇林端起酒杯敬媒人:“托你的福。” 又敬姑娘:“祝你的福。” “这家里就缺一个料理日子的,我是看着青娃子长大的,本分勤快,不惹是非,尊老爱幼的好后生,”根山老爷杯酒落肚,直夸树青:“来,掌柜的,也祝你福如东海啦。” 姑爷接了酒,忘记脚下残疾,一个趔趄,酒洒了一地。他忙抖擦弄湿的衣裳。众人举杯来敬,他把酒端到媒婆面前:“敬红人。” 众人挨零敬过,他们把媒人灌醉了。 我背了书包去上学,见树青和琼芳在荷塘边的柳树下说话,心头喜不自禁。 下午放了学早早的回去,这天心里很高兴,我也喜欢表嫂,不只是他漂亮,象热了一夏的天一下凉爽起来。 到了铺子上,见赵中发正在装枪,火机关开着,上了炸药,用铁铳在枪筒里筑实了铁沙子,对姑爷说:“打着了,打平伙,你出烧酒。” 我来不及放书包,便尾随赵中发朝荷塘的沟边走。要到了沟边的柳树,赵中发叫我不要跟了,我只得卧在一块石包后,看他猫着腰接近猎物,一只白鹤正在柳枝上向水田那边张望。赵中发刚要举枪瞄准,白鹤奇怪的朝我们的方向飞来,赵中发开枪打飞火,白鹤中弹落在了茶馆的竹林上,青狗老表忙拿了晒衣竿把它戳了下来,撵山狗一口抢了它,衔着朝赵中发跑去。 我问青狗老表,表嫂呢?走了。 赵中发提了白鹤回来,交给老表说:“太小了,你拔了毛炊着,下回待客。” 我接了白鹤,把他腋下的绒毛扯了,用纸包上给姑爷,鹤绒止血奇好,特别是创伤,时常有人讨要,姑爷就给些。干拔了鹤毛,在灶堂上燎了一下,就干净了,交老表挂到灶搭勾上炊干。 我把竹林里的竹椅茶桌,抬来码到干檐上,扫了地,走到姑爷的铺子上。想从姑爷的脸上知道表嫂的一点消息,他还是平常的脸色。看今天中午的情形树青和琼芳的媒是成了的,突然没有了结果呢? 晚上的时候,我想到表嫂,觉得她就在莲塘的柳树下。鬼使神差的起来,看见月光在莲塘酿一层白雾,一只孤独的白鹤在柳梢上,白天赵中发打的白鹤是不是他的爱侣呢?我偷偷的联想起来,觉得表嫂再也不会出现了。 半月以后,表嫂的消息几乎没有了。茶客们偶尔的议论,我还希望着,他们有时会问老表或者姑爷,老表和姑爷总是说:“琼芳,她忙。”后来大家都缄口了,若再问老表和姑爷,是对父子的挖苦,大家心照不宣总把话题扯到一边。 我回屋拉着老表,问他:相亲那天,表嫂给他说过什么没有? 老表说:“她还想教书。” 如果她去教书了,就不可能成其为表嫂了。 媒人一直没有回话,这让老表心里像打秋千。 表嫂是桂山人。我班有一个桂山的同学,他认得琼芳。 放暑假了,我便和同学去了桂山。 桂山在西岭,同学的自行车搭着我走了二小时才到。他家在猪坳口,再转过石堰子才是琼芳的家。到了同学家,他先爬上李子树,摘了半包李子下来让我吃。我说:现在就去琼芳家。同学便吆了牛,朝石堰子走。 石堰子水库,在两山的夹槽里。琼芳家的山草房修在水库边的山岩下,陈年的山草房平实地掩隐在斑竹林中。她父亲是石匠,正在院后的石场打猪槽,一架独轮鸡公车上盖着茅草。隔二天他就把猪槽用鸡公车推到山下的乡场去卖。 明全把牛拴了,带我走到石场:“打石爸,歇哈气嘛” “哎,在歇气,你看牛啊,放假了。” “嗯。” 石匠说话并不停手上的活,只抬头看我们一眼。他戴着风镜防石渣灰,让人感觉很洋盘。一根烧了半截的叶子烟旮在耳朵上,赤裸的上身黑得淌着油汗,肩上搭着的毛巾已无正经的颜色,毛毕叽裤子泛着一层白色的汗花,那花染成银元似一圈一圈的地图,不断在扩张濡浸,脚上的草鞋快磨穿了底子。 “琼芳姐,在屋头没有呢?” “在,又找她借书?” 我们下坡进了石院子,石院子上的破瓦钵栽着金边兰,紧靠着毛楠树,斑竹林的竹叶飘落在了院子,象泊满了舟船的港湾。屋的窗是斑竹做的肋巴骨,琼芳正坐在窗下看书。 “琼芳姐。” “哎,”抬头看见是我,说:“你好久来的呢?” “我们是同学。” 她,穿了短袖的春纺衬衣,脸色清瘦了,留海长得遮了眉毛,眼神悒郁罩着青影,她起身扯了扯衣摆,站起来忙给我们端凳。 我借花献佛,把同学的李子送给她吃。 她从屋里抱出些图书和杂志,还有几本小说给我们看,我翻着《中国青年》杂志,一边偷看她,她似乎觉察到了我的眼光,向我凝神稍许,又看她的书。她要赶在明年招民办教师的机会再争取一次,她相信天下的乌鸦不是一般的黑。 每本书上都留有她的签名文字,字迹娟秀流利。我没有指望她做我的表嫂,理想不能生长在开花的季节,好比嫩青菜砍下来渍成盐菜。只是下饭菜。 在一本古典文学的空白处,我读到了他的一首词: 豆荚瓜藤处处栽,柴门锁扣久未开。一雨经宵庭草长,上石阶。 山色故作云姿态,好风常与月相偕。小犬隔林遥吠影,有人来。 临别的时候,琼芳姐送我们到水库边,一棵李子树下站着她单薄的身影,我说:“琼芳姐......”想说她到街上来耍,想说我们很想她,想说你一定能考上老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像水库虚映着山上的枯树。 回到街上,姑爷拄着他的拐棍在铺子上,跛来跛去,青狗用纱布擦着那把铜壶,我把几棵李子给老表,替他擦铜壶,我可怜我的老表和姑爷,还有琼芳姐,更可怜自己。 每天,我不再象以前一样打兔翻玩,喜欢上了看书。让同学在琼芳姐哪里借来看,更多的时候是看她留在书上的文字。躺在床上,看倦了就把书盖在脸上,可以闻到她的手迹和气息,这样我可以知道她这段时间在做什么,感觉她的生活。 第二年春天,我就把她的书借来看完了。满山的桃花和李花开得繁茂,白蝴蝶也常飞到场口的一棵歪脖子老李树上,是不是石堰子琼芳家那棵李树上飞来的蝴蝶?我常常看见本来就开花很少的老李,唯有一只蝴蝶天天在飞。可惜李子莫待成熟就遭虫落光了。 三、满塘烟水 初二时侯,我们学校调来了一位川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老师姓蔡,本来是分到县城教高中的,却愿意到乡镇上来,图的是清闲。到了星期天,蔡老师似乎与别的老师格格不入,常一个人到山上或乡下去逗留。见我住在街上,约我到学校的后山去给他陪伴。渐渐我才懂得他的性格是自由散漫随性的哪种,有时他请我去吃馆子,酒后念一些狷狂或愤青的诗,常常语惊四座。 在夏天,蔡老师放学以后都来茶馆约我,姑爷高兴学生被老师器重,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乐意让我去陪他。我们各人抬了椅子到柳树下莲塘边喝茶,这引起了人们的新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学校的老师,也模仿要求老表把茶桌搬到沟边的柳树下,茶涨到一角五分钱一杯,是原来的五倍。姑爷又新增了桌椅,讲究体面的人都去了莲塘柳树下,老茶客还是在竹林里。乡政府的乡长带着县领导到莲塘的柳树下喝过一回茶,这在乡镇上引起了一阵轰动,觉得新鲜,很看高“拐子茶馆”。姑爷和老表合计了一下,用石灰把旧房粉刷了一番,骆宇林又把旧瓦翻新了一遍,吊檐刷了一层红漆,墙上的穿疵漏眼都给补平。父亲又送来几根树子,姑爷请来木匠打了几个货柜,把商品放在嵌了玻璃的柜子里,把那些吊吊窜窜落满灰尘的薄膜口袋全取了下来,屋子显得亮堂了。 在乡场上居民的眼中,“拐子茶馆”似乎翻身了。姑爷心情好给我制了一件“的确良”的衬衣。老表也解了常年拴在胸口前的围腰帕,蓄起了“三七开,分分头”。原来三分钱一杯的茶统一提到五分,人们还是乐意来。蔡老师给拐子茶馆提了一副对联: 趣言能适意, 茶品可清心。 初中毕业的暑假,在蔡老师的辅导下,我的中考作文得了满分,正在等录取通知书。蔡老师家在外地,也不急着回去,把伙食都安在茶馆,大家更亲密无间。晚上他也不回冷清的学校和我住在一起。 一天蔡老师给了钱,让我去馆子弄些下酒菜。在黄葛树下的馆子前碰到琼芳的父亲在树下卖猪槽,给他打招呼,半天才想起我去年到过他家,买了下酒菜随手抓了两把水子花生给他。刚要走,迎面看见琼芳从供销社买了书走出来,她见了我提着菜,问:“家里来客了?” “嗯,你就是客人,买来招待你的。” 她父亲在树下看见我们说话,便喊她。 我随她走到树下,正好有一个熟人来买猪槽。石匠喊价五元,那人只给三元, “双槽才八元一块,单槽三元差不多。” “单槽、双槽的工并不少多少,石头材料不值钱,贵在功夫。” “河生大爷,你添一元钱买了,多长几斤猪肉,多的都赚回来了。石匠伯就让一元,添一元的少一元,大家都撇脱。” “你娃会说话,将就娃说的,四元就给四元。” “好、好、我还要赶回家。” 卖了猪槽石匠推了鸡公车,朝场口走。到了“拐子茶馆”门口,我拉父女俩进去坐一会,喝碗茶。姑爷见了,忙走出来劝客。琼芳的父亲并不知道缘由,见太阳正刚,对琼芳说:“喝碗茶走。” 琼芳只得随了进来。她戴着白草帽穿白色的连衣裙,走到竹林里,坐在椅子上的蔡老师吃了一惊。琼芳揭了草帽挂在衣竿上,我去给她们倒洗脸水,姑爷拿来一张新毛巾,还有玫瑰香皂。 青狗老表在灶房煮饭,听到说话声走出来,没想到是琼芳,相互点头招呼。姑爷拿出纸烟给石匠点燃,又招呼蔡老师抽烟,老表给石匠泡了清溪茶。 琼芳坐在檐下,往屋里扫瞄,感到焕然一新。蔡老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可她一点都不在意。我叫她到屋里坐,把吊扇给父女俩打开,她汗湿的头发在鬓边飘飞,荷叶领象蝴蝶翩然起舞,天热烤红的脸回复到粉红。她一边看老表在隔窗的灶台忙碌,一边欣赏着墙上的电影片断剧照。偶尔瞟一眼戴眼镜一直看她的蔡老师。我说:“蔡老师,进来吹风吧。” “不了,竹林自然风,也凉快。”又招手让我过去。 我提了炊壶给他渗水,他拉了我在耳边问: “是你姐姐?” “嗯……” 我又去堂上给他们续茶水,姑爷坐在桌边正无措,石匠也直夸生意做得好。我坐在空方位翻看琼芳买的书,一本王国维著的《人间词话》。她问: “毕业了,考的如何?” “要下月二十五号才知道” “你同学说你考的好。” “我的老师才知道。”我指指蔡老师。 她正经看了蔡老师一眼。 老表说饭菜好了,我忙去帮忙上菜。 四方桌上,我和蔡老师一方,对面是琼芳姐和她父亲。左右坐的是姑爷父子。 一桌六人,吃得都拘束。 饭后,琼芳帮忙收拾了碗筷。下午,蔡老师回学校去了。 我和老表、琼芳姐上街。她买了一件新衣,我们吃了冰粉才回来。茶桌上,姑爷和石匠也谈得差不多了,几个老茶客正在开玩笑说: “拐老兄,今天起,你就是烧火大爷了。” 姑爷指指在坐的石匠,说话人脸上一红,忙打着了话头,明白石匠就是琼芳的父亲,收敛了黄腔。 太阳落山的时候,蔡老师来到了茶馆,手里拿着他新填的词,拿给我欣赏。我看过又拿给琼芳姐看,她看吧,对蔡老师另眼相看。可时候不待,他们要回去了,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 姑爷高矮塞了一包香烟给石匠,我们把父女俩送到场口的路上,琼芳姐把蔡老师新填的词夹在《人间词话》也带走了。他耀眼的白草帽随着独轮鸡公车的干叫声在山路上盘旋,最后消失在暮色中。 乡场的场期是一星期一场。下一个星期,琼芳又来到了茶馆,说是来还蔡老师写的词,时不凑巧,蔡老师去了县城。我说他下午会回来,挽留她吃了午饭。下午太阳阴了的时候,她和老表在柳塘边逗留了一会,就去了山上的枞树林。姑爷的心底乐意,见打枪子赵中发提了一只野兔进来,姑爷说要了,给了他三元钱。他拿了一包八分钱的“经济烟”,喝了一口凉茶,邀约了其他几个打枪子,去尹家湾的秧田打屯鸡,说是今天有人发现了一群屯鸡在田坝头。七八条青的黑的撵山狗伸着长舌,“嘿嘿嘿”地喘着粗气,枪耳子竖起来,像战士出征的雄赳赳。打枪子在铺子上买足了“军火”,裤儿挽齐大胯,朝尹家湾出发了。 房子匠骆宇林去汤槽盖房子回来,肩上扛着梳板,喝了烧酒尔浮尔浮地一脚高一脚低,腰间的刀盒子在屁股上“嗒吧”响着。今天收工,结了工钱来把往日的赊账结清,姑爷说:“骆宇林,小见了,收你钱啦。” “有钱还账天经地义,只是不好意思拖你太久。”说着他提一条冬葫子放到柜台上。“老哥子,这家主人落教,工钱给够,酒足饭饱,还送一根冬葫子,送老哥子拿去烧汤。” “拿回去吧,加点面疙瘩,一家人就又过一顿了。” “不,我要送你,嫌弃了?” “好。”随手在玻璃瓶子抓了把水果糖,塞在骆宇林的衣包里。“不早了,明天来喝茶。”假意推他一把,骆宇林就走出了场口。 这时街上的人都坐在门坎上摇风打扇,年轻的去了塘边上乘凉,有人高声的说笑隐隐的传来。 晚上十点过,树青和琼芳才回来,姑爷问他们吃饭了没有?树青说,没有。 我便穿了拖片鞋,把赵中发提来的野兔吊在檐口上剥了皮,剁碎和冬葫子一起炒了,给他们煮饭。他们在竹林里坐了一会,退了凉。老表放了一盆洗澡水,端到里屋,让琼芳洗澡。里屋的灯灭着,只听见水的哗啦传来香皂的玫瑰香。心细的姑爷睡在铺子上,拿来洗发香波,叫树青给琼芳送去。老表接过洗发香波,隔窗喊叫:“洗发香波。” 窗帘子伸出一只手接着了。 饭菜做好端上桌,头巾拢着湿发的琼芳,象宋代词人笔下的沐浴女婉约清丽。老表说:再吃点。我说,吃过了。 躺在床上听他们吃饭说话的声音,渐渐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老表挤上床,叫我往里辗点。一下醒来,才想起还有琼方姐呢,“在隔壁。” 我听到隔壁的灯:“嗒”地灭了。隔着一张墙板,隐隐听到她的呼吸,翻身的床草响过,似乎又一声叹息。 昨夜天热,第二天是咸天(闲场),都起得迟。起来的时候,琼芳已起来了,在檐口的洗脸架上梳头,她把长发编成辫子在头上盘成一个髻显得高挑而又挺拔,穿上昨天老表给她买的一件立领衫,前襟和袖口打了折皱裙纹,像欧洲的贵族女儿。 吃饭的时候,琼芳第一次叫姑爷:“干大。”(农村未婚媳妇对未来公公的称谓。) 这使姑爷很激动,老表的婚事终于有了定音。 姑爷大张旗鼓地通知了亲戚朋友,我骑自行车去把琼芳的父母请来。蔡老师也参加了老表的订婚席。定婚的规格按时下结婚流行的“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收录机。还有冬夏各一套新衣。那些天,小镇上很喧哗,本来出类拔萃的表嫂,足以引人注目,再给不名一文的青狗耍朋友,就是一条爆炸性新闻,在山乡象爆鸡婆下蛋,咯咯咯传开了。这个结果连媒人都不知道。 准表嫂来的第三天,就给姑爷建议新修两间新房,姑爷考虑后答应了。新房半月后就建成了,背靠着屠宰房,隔断了那边的腥臭。新房是青砖瓦房。亲家石匠又来帮忙打了炉灶,从竹林的出山处修整了一条出路,乡坝头来的自行车,扁担筐筐就可以寄在这里。 到了下个月,瞎子择了黄道吉日,一家【琼芳酒家】的馆子就开张了。 馆子成了主业,茶铺就退居到了副业。表嫂伙食弄得干净,又与屠宰房挨邻则近,割肉既便宜又充足,菜品价格也公道。一段时间下来,生意已赶上正街有名的“味道鲜”馆子。表嫂的名气也跟着上涨。特别是赵中发一帮打枪子的野味,是一道招牌菜,政府的领导下来都来光顾生意。土地下用水泥石抹了,在客堂布置了蔡老师的书画,尤显高雅气。茶馆日新月异的巨变,格外佩服表嫂的能耐。 在城里读书少有去姑爷家了,但姑爷还把我当亲人,时常挂念着我。放了暑假,赵中发到家里带来姑爷的信,要我到街上去一趟。 我到茶馆的时候,姑爷不在。门口“拐子茶馆”几个字已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金字招牌“琼芳酒家”堂而皇之。堂子的柱上一副对联: 有花方酌酒, 无月不登楼。 一看就是蔡老师的手笔。 家里只有表嫂一人。她的长辫已剪了烫成卷发,比以前胖了一些,尤其白嫩,光鲜的料子衣裳穿在身上更显得漂亮。她伏在桌上写字,早就听说她在复习迎考。 “表嫂。” “哎,老表,稀客。” “还在钻书。” “看一下《函数》,有些都忘了。” “姑爷他们呢?” “病了,在医院。” 我走过她身边,把礼物放到桌上。以前她还高我半个头,现在我比她还高些,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 “我到医院看下姑爷。” 表嫂弹掉我衣服上的一条毛虫。表嫂才二十二岁,正值青春,过早的成熟,让她的眼里有一丝苍桑。 在医院里,老表扶着姑爷刚打完针到病房。见我来了,姑爷对树青说: “你回去照看生意。” 树青老表走了,姑爷拉着我的手:“长高了,一会不来就想你。” “读书太远,也难的回家。” “把书读好最重要。你表嫂也复习功课准备去考大学。”说过叹了口长气。 看着姑爷,知道他内心的忧虑,也不知道老表咋还没给琼芳结婚,姑爷找我来说的怕就是这件大事。 “你放假没事就在这多耍二天,你不晓的我们家。这一向都沉闷得很,心里都打了肚皮官司。” “蔡老师还常来吗?” “来。” 晚上,姑爷出院了。大家好久没有这样团聚过,表嫂格外的高兴。学校的操场坝子今天晚上放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吃过晚饭,姑爷说:“你们都去看电影,我在家守屋。” 我们抬了高板凳到操场上。学生已在前面安了一排凳子,通往乡场的几条路上,群众像蚂蚁一样朝操场上汇聚,在场口上已打涌堂,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夹杂着惊呼呐喊的声音。骑自行车的在香樟树下成了一道风景,大家展示着“凤凰”和“永久”围观的人投来羡慕的目光,穿得伸抖舒气的姑娘小伙,互相问好。手一捞“上海表”,脚一抬“永久牌”,都很“港”。电影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把自行车架起来当凳子,比高似的有的站在了车架上。 电影开始。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新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故事片叙述了,沈荒妹的姐姐沈存妮和小豹子相好,在公房的草堆做了切肤之亲的事,被村上的人双双捉着,沈存妮受不了流言蜚语而自杀,小豹子在抓捕时逃亡天涯。从此沈荒妹视男人为恶毒,从不与搭话。村上当兵回来的许荣树,爱上了沈荒妹。沈荒妹在恐惧中因家庭贫困负债,被母亲以五百元的彩礼许配给了外村人,许荣树得知了站在山头,远望着渐行渐远的沈荒妹...... 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 爱情将它久久遗忘, 当年它曾在村上徘徊, 徘徊。 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 表嫂看到这里,说出去一下,离开了电影场。 ……当沈荒妹挣脱母亲的手,跑回村里的时候,全场的人雷鸣般的掌声喧哗起来。 电影完了,表嫂一直没有回来,我和老表走到场口,才见表嫂拢屋。 老表住在我原来的房间,和他的房间相通只是一门之隔。老表第二天五点就起床,在馆子忙开了。 表嫂起来,梳洗巴适,便靠在茶桌上看书。姑爷拄着拐棍忙着择菜,老表忙墩子。我帮忙打扫卫生,摆好竹椅板凳,把昨天一盆的碗筷洗了。老表无怨无悔地做着,好象没有表嫂这个人。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忙过后,二点过才吃午饭。吃饭放了碗筷,表嫂又去看书。见她心神不定,一边看竹林外的莲塘,一边在笔记本上写划。五点过后表嫂又出去了。问老表,老表说是她去请教蔡老师去了。 我去表嫂的房间拿书看,发现她独居一室,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表嫂做了一个美观的书柜,书摆放得整齐归一。一本绿壳的笔记本随意的放在写字台上。我随便翻了一下,见写了一首词,时间是昨晚写的: 满塘烟水月微渺,人倚竹竿小,常记相逢桥边上。 隔三天,碧云望断空惆怅。 流水笑道:莲花相似,情短藕丝长。 我放了笔记,径直去了学校,没有找到蔡老师,一人独自爬到学校后山的青冈林。隐隐看见表嫂粉红的身影正和蔡老师在树下说话。蔡老师看见了我,我便向他招呼,表嫂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忙从背后拿出《函数》书。 蔡老师问过我的学习说:“你这下回来了,你表嫂就有现存的老师了。” 三人慢慢走回学校,学校已放学了。到了蔡老师的寝室,推门就看见表嫂的画像,背景是荷塘和柳树,她的形象显得超凡脱俗。题款是一首残词: 摇落最怜溪边树,云到天涯,何处无风雨。 休共浮萍流水处,莲房自守芳心苦。 收回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一叠试卷,是表嫂做的高考模拟试题,上面有蔡老师的圈点。 临别,蔡老师交了一叠卷子给表嫂,是他从书中选择的试题,要表嫂把方程式的解法再强化一下。走在街上的时候,人们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和表嫂。 姑爷和老表己吃过了午饭,见我和表嫂一路回来,饭菜凉了,忙叫吃饭。 和表嫂一桌吃饭,她总是停筷看着我,我摸摸自己的脸并没有什么,她抿嘴一笑,把头扭向一边。我说: “笑啥子。” “我想起那年你到我家来,是为啥子?” “……” 吃了饭,老表把我拉进屋里说:“你来了,她才开心,你多陪她聊聊天,多谢了,老表。” 我拍着老表的肩,衣下是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脸上的表情楚楚可怜。 表嫂正好进来,把那本放在写字台上的绿壳笔记本放回书柜,拿了一把扇子走出去了。 尾随表嫂的脚步,她来到莲塘柳树边的石桥上,看着漫天蜻蜓追逐着望水蛾。“农业学大寨”的五个字渐渐隐匿苍黛,水田里青蛙跳水的姿式,让我想起童年,成长使人生出感伤。 “表嫂,我告诉你,那年去你家的原因。” “哦,‘槐荫树’”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开玩笑,你才好大点。” 她看着高她半个头的我,脸上的嘻笑凝固了。她不过大我四岁,我正是她当年的年龄。 “……喜欢你是我的表嫂。” “我晓得你装怪。” 他摇着扇子给我打风,这时乡站广播传来《角落之歌》: 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 春天已将它久久遗忘。 当年他曾在山头停留 停留。 到何时他再愿来此探望, 嗯...... 山坳口吹过来一阵风,把秧田掀起一片绿浪,带着水腥气灌进了场口。屠宰房里一阵杀猪的叫声,鲜血接了西街瓦房上的云霞,回光返照在表嫂的身上,仿佛镀了金身的女菩萨。 我高中毕业的时侯,表嫂考上了哈尔滨大学。 青狗老表送她到成都转火车,把身上的钱一分不留地给了表嫂,从成都走路回来己是第二天下午了。 表嫂年年都要回来,看望姑爷和老表。茶馆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张漂亮男孩的照片,老表说是他的儿子,姑爷也逢人就说是他的乖孙。 姑爷死的时候,表嫂哭得伤心。立的碑上写着儿媳:琼芳。 如今老表已六十多岁了,表嫂给他买了社保。他象当年的姑爷一样依然守着茶馆。书樻还给表嫂留着,保持干净整洁。 赞 (散文编辑:可儿) |